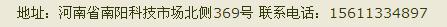好贴回顾拖大的一辈记一个家庭与一座城市
第一章无辜的生命
第二章黄金棍儿
第三章好不容易发萌
第四章哥哥是我们的头儿
第五章逆反心理
第六章一碗豆渣
第七章外婆,还有外婆和那些婆婆大娘们喜欢的人
第八章大舅和他的家人
第九章那一刻,我真的不觉得死有啥可怕
第十章搞不懂的政治
第十一章大姐姐
第十二章三十二斤和六斤
第十三章外公
第十四章三舅和二舅
第十五章甲子年
第十六章担担面,我心中永远的一道风景线
“无辜的生命(一)”
我一直以为我是家里最受宠的一个,除了死去的弟弟渝儿。
其实渝儿死得很早,他只活了两岁,也只比我小两岁,和共和国同一年诞生,就在一天清晨,死在了我的脚下。
关於他,我的记忆非常模糊;瘦瘦的,很单薄的身子,大眼睛里总是闪着逗人怜爱的光。我记得,走出家门就是菜场,菜场的尽头有一个冰糕厂,大些了才听外婆说那是较场口附近的石灰寺街。街的这一段后来拆掉了,修了一个带街心花园的大转盘。
天气炎热的下午,我就带着渝儿去冰糕厂门口,那厂也很简陋,没有正式的大门,就一间特大的生产冰糕的房子。房子的门开得很大,还是双扇的,门上挂着两排厚重的宽条,就象现在有冷气的建筑物对外要打开大门挂的那种塑料膜。我也弄不清楚那挂的是什么材料,只记得我和渝儿往宽条边一站,也不用开腔,看厂里的人忙,忙完了就有一个老头儿会走过来递两只冰糕给我们,还笑着问我们:“喜欢吃冰糕阿?”
我不回答,低着头只顾去吃,渝儿自然也不开腔,只是怯怯的闪着大眼睛。我从来都没想过,那老头儿为什么会给我们冰糕。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才去想,却始终也想不明白:那老头是喜欢我呢,还是被渝儿招人怜爱的大眼睛感动,才给我俩冰糕的。
也就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渝儿死了。
“无辜的生命(二)”
我和渝儿睡在同一张矮矮的单人床上,一人睡一头,抵脚而眠。突然一个大清早,天才麻麻亮,我就被外婆拍醒了。
外婆的薄嘴唇对着我不停的翕动,气急败坏的大声吼道:“你咋个睡得这么死哟,你弟弟渝儿都死硬了,就死在你脚下你都不晓得!”她的一只瞎眼在黑暗中象一个洞,幽幽的没有光,很恐怖的对着我。
我往脚下望了一眼,只见一堆黑乎乎的老蓝布裹着的小身子团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阵恐惧从我心里涌起,我张开口就哇哇哇大叫起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哥哥弟弟妹妹,就经常听妈妈数落我们:“渝儿比你们听话多了,好多了哇,哪里像你们这样哟!”
当然,妈妈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渝儿虽说是她第三个孩子,却是完全由她亲手带过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生的五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完全由她带的孩子。大哥和我,是保姆带,小弟是奶妈带,小妹却是由外婆一手带大。
每一次妈妈这样说,外婆的脸就暗了下来,然后是双手把头一抱,屁股往床里面一耸,吊着脚坐在床上。突然,她会放开双手,翘起嘴说:“我还不是喊的摇串铃过路的阿,我还是找人把他抱到正而八经的诊所去看的呀!他就只是个咳嗽过嘛,又咳得不凶,又莫得啥子大病,”外婆把身子往后一仰,两手一摊;“那个会想到他头天晚上吃了药,还没等到第二天,我是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去看的,就死得梆翘硬了歪!弄不清楚那些是些啥子鸡巴医生,拿的是些啥子鸡巴药!”
妹妹咕咕咕的笑,笑外婆说话带霸子,我却稳起,什么表示也没有,心里却想:听到这种怪话,就是笑,也不好,我这样想。
渝儿的死至今是个迷,外婆目不识丁,始终说不清楚他怎么会死。后来,家里的人都说成是医生拿错了药他吃后死了的,终於给外婆卸掉了主要责任。母亲参加过土改,懂得可以告,还问过外婆:“那为啥子不去告那医生咧?”
这是渝儿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影像,摄于年。
“无辜的生命(三)”
第一次听到这话,外婆愣了!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即一八九八年的外婆,祖祖辈辈都是国家的顺民良民,心地慈善,她完全没有这根筋,遇事还要去告人!
开玩笑!要起诉讼,是要花很多钱的,银子哪来?再说,她也没有这么恶;告人咯,那是要送人下大狱上断头台的事阿。即或医生拿错了药,他也不会是故意的。人生在世,谁会没有个错嘛!
渝儿的小生命太微弱了,没有引起外婆“关天”的感觉和联想。渝儿的弱不仅在于她只有两岁,还在于急着去当兵的母亲,要把孩子全都托附出去。父亲不谙家务和带孩子,又要上班,只领走了大哥,母亲只好把我和渝儿交给了外婆。我俩跟着外婆才一个来月,就出事了。渝儿成了外婆带过的所有孩子中,相处得最短的一个。
外婆也还没有来得及和渝儿建立啥子感情,他就走了。渝儿的死只引来外婆一声长叹。外婆无意识地对待生命大与小的不同,却不知不觉深入了我过于稚嫩而又毫无分辨防范能力的内心,我也毫无意识的用这种不同去对待大小生命。直到几十年后,我飞出了国门,才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是就是了,兵荒马乱的,到哪去告啊!”渝儿死时,国家正忙着抗美援朝,母亲正忙着在部队上剿匪。虽说是已解放了两年,却没有人来搭理这档子事,母亲只好这样替外婆回答。
一个两年的生命,在人为的疏漏下,微不足道地被无辜淘汰出了尘世。
“无辜的生命(四)”
从国势衰落的晚清一路走来,外婆的大半生都是在战乱中渡过,她不是没有经过世事,同样,外婆也不是没有见过孩子。她生养了九男三女,用她的话说,日妈现在,这几个娃儿就蹬打不开了,还做啥子事哟!她象一头历经生死场的老母猪,带领着她的猪崽们大刀阔斧的向土地向社会讨过生活。尽管如此,我却只见到四个舅舅和我妈妈,其余的都夭折了,而且都是长到了十七八岁才去世,生存的艰辛也就不言而喻。
外婆信佛,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渝儿的死,外婆有她的一套说法;孩子都是一样的带,能不能长大,有没有福寿,那就要看阎王爷的安排和自己的造化了。象渝儿这种孩子,逗人喜爱,又活不长,是来讨债的,是你前世欠了他的。天长日久,三人成虎,母亲便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渝儿再好,也是死了阿,活着的四个当中,在家里却没有谁能和我比,爸爸妈妈外婆外公舅舅舅妈们,都是最喜欢我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可是直到耳顺之年,我才明白,我错了!兄弟妹妹亲戚们心里都明镜似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掉进了无底深渊;无所依旁,无人在乎,无法求助。就这样在空中落阿落阿,不知何时是了。
上了年纪的人,不是一个容易敞开心扉的年纪,也不是一个喜欢交朋结友容易寻欢作乐的年纪,在这个年纪才意思到的空落,不容易排遣!这意思到的却又是因为妈妈的病危引起的,我开始从根上去寻找,去思索。
错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是从渝儿死后开始的吧,我想。因为他死之前的事,我就只记得带他吃冰糕。记忆是由他的死才开始的,那么错觉也应该是从有记忆才开始的吧。
“无辜的生命(五)”
回溯过去,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个个片段的镜头,却寻找不到连成这些镜头的线索。
渝儿死后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穿着一条薄薄的单裤,一双露出四个脚趾头的破布鞋,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清鼻涕掉掉的站在一只没有船篷的旧木船船舱里过河,河风呼呼的吹得我浑身透凉。一个尖嘴猴腮的人站在我的左前方,一身半新旧的蓝布长衫,大声武气地对我说:“你看你那鞋,都破成啥子咯,实在难看死了,还不如打光脚。你马上就要看到你妈了,穿这样的鞋去见你妈,也太丢人了嘛!快脱下来丢到河里去。”
我低着头,发痴的看从破鞋头里露出的四个脚趾头,红红肿肿的,满是冻疮,却不愿意脱。鞋前面虽破了,鞋帮子却是好的,多少能护着脚背脚边脚底板,总比打光脚好哇。我心里想。
“你这娃儿也犟,叫你脱硬不脱。哼!”尖嘴猴腮生气了,又对我凶了一句,便调过头去不理我了。我不安地低着头,却还是不愿意脱下鞋来;我害怕光着脚去踩结满冰凌子的船板。
船靠了岸,尖嘴猴腮带着我走上岸边冰冷的石台阶,我暗自庆幸没有脱鞋,否则咋个爬这台阶哟!我们爬完坡,站在码头上石台阶的当中,四下观望起来。船小,过河的人也不多,很快人就走散了,只留下我和尖嘴猴腮还在那里观望,观望。尖嘴猴腮已经开始不耐烦地嘟哝起来:“咋个咧嘛,不是说好了这班船……”
“无辜的生命(六)”
我对妈妈毫无印象,也搞不清楚为啥子我会这个样子被送到这里来,只是任人摆布听天由命地站在那里。尖嘴猴腮着急,我也冻得受不了的跟着着急,咋个咧嘛……。我想尽快离开这冻死人的码头。
突然,一个干净整洁、浑身散发出热气和温暖的美丽女人,满面笑容,穿着紧身的绵军装,扑到我脚跟前。她的笑立时凝在了脸上:“哎呀,咋个搞成这个样子嘛!”她的双手拉住我的双手,立刻一股暖流传到了我冰冷的小手心。
“快,快叫妈妈呀!这是你妈。快叫呀!”尖嘴猴腮赶紧催促我。我却低着头,稀开了嘴,牙齿上下很响地嗑嗑嗑打着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妈妈拉住我的双手张开来,蹲下来打量我,然后一把把我揽入怀里,用她红扑扑香喷喷,那是干净暖和的清香,还有暖融融的冒着热气的脸贴住我冷冰冰脏兮兮,还鼻涕拉撒的脸。我也趁势死死地贴住她不放。
我太冷了,冷得什么也没有想;只想取暖。我的头不自觉地就爬在了妈妈的肩上,冰冷的双手紧紧的圈住了妈妈的热呼呼的颈项。这样一来,我便是背对着尖嘴猴腮了,再也不用看那张讨厌的脸。但我听见妈妈在对他说了些“谢谢你咯”之类的话,便抱着我离开了码头……
未完待续,请进原帖阅读
涯叔提示↓↓↓点击阅读原文
赞赏
长按
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cs/124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