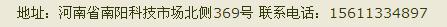首届昭明文学奖参赛作品选寻找清莲小
寻找清莲(小说)
储彪
1
梅梅突然就恼了。怎么会呢,明明上楼时还在办公桌上,一扭头的功夫,就像施了障眼法,说不见就不见了。她板起脸,眼睛里遽然间全都结满了冰,一坨坨砸下去,砸得男孩缩成一只小虾球,团在那里不敢动。见此光景,她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手一伸说,把文具盒拿出来。男孩眼皮耷成破旧的窗帘,只在帘子遮不住的底沿,露出一缕弱小动物眼睛里才有的躲躲闪闪的光,伸出两只猴爪似的小手,从斜挎在胸前的油腻小包里,把那只清新爽亮的文具盒,抖抖簌簌放在桌上。梅梅一动不动,双手抱在胸前,眼神端端的直视在高处,似两枚冷硬的水泥钢钉,钉在雪白的墙上。时间肯定不长,但那种冷凝的姿态把时间的直线冻得弯弯曲曲,成为拆迁工地上堆砌的废旧钢筋,凌乱不堪地压在那儿。待她收回目光,重新将时间的曲线捋直时,男孩已从眼前消失,只有无声无息卧着的文具盒,证明一个孩子曾经的存在。
早晨,梅梅从漫漫苦熬中刚刚找到一点睡眠的感觉,黑脸差子便把光了一夜的热身子压上来,脸上的笑虽然荡着水一样的柔波,可身上那根昂然挺立的宝贝,还是显出了男人的霸气。她偏不给他霸气,屁股一扭,肚子一挺,就将那具光溜溜的热身子闪到一侧。
十一月中旬的朝阳仿佛是只寡淹淡渍的鸭蛋黄,没有油不说,连那种红亮的颜色也比往日薄了许多。偶有一片两片吊在枝头的树叶,苦着张输光了衣裤的赌徒脸子,瞅着勾头缩肩的路人,抖索出满树的寒意。
对梅梅而言,今天算一次早起。起得早,不等于就去做早饭。她的早饭,都是黑脸差子的宝贝真正成为宝贝时她才做。今儿不,她来到小吃街上,草草吃过便上班去了。快到办公楼时,听到身后有小孩喊,等等姨,手套。她左右张眼看看,往来的都是男人,一个个嘴里喷着热气,像被欲火烧狂的公牛,不由想起被掀翻在床的黑脸差子,心倒顺了几分。停住脚,回过身时,梅梅脸上已有了暖意。只见一个八九岁男孩,手举一副手套,连走带跑着撵上来,蓬乱的头发像只鸟窝在耸动。
姨,手套你忘了。见她等在那儿,男孩松了步子,连喘几口雾气,红着一张小脸说道。
梅梅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戴手套出的门。一碗热稀饭还真是顶用,吃罢起身就走,竟也未觉出凉来。她接过手套,重新戴好,这才笑吟吟道一声谢谢。边说,边从包里掏一块钱硬币,塞到男孩手里。男孩接过钱,本是倒置的梨形脸立刻笑成了圆蒸包,从豁牙里往外冒热气。
吃早点时,男孩伸着手走到跟前,她想都没想就把一只热乎乎的茶鸡蛋给了他。男孩似一只饿了仨月的陌上小蛇,伸长脖子,三口两口吞进肚子,随即又伸出了手。梅梅的不快跟着就来了,说你看,我就买一个,才给过你,还要啥?他低着头,声音细成了一只蚊子腿,给俺一块钱吧。若在平时,梅梅肯定会给他。可今天她也不知怎么了,烦得话没听完,抓起单肩包就走。现在想想,何必跟个乞讨的孩子较真呢。
梅梅伏下身子,笑着问,怎么不上学啊?男孩告诉她,很小的时候去车站,姐让坐候车室等她,不准乱跑。他坐了几天几夜,哭醒了睡,睡醒了哭,他倒是听话,坐成一只蘑菇,长在候车室长长的连椅上,却没有等到姐,没有等到姐每天哄他睡觉时讲的,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后来,他就到处找姐。梅梅心一凛,说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呀。爸爸妈妈早死了。爷爷奶奶呢?也死了,他说他是姐带大的。叔叔舅舅,还有姑姑,姨娘呢?他撇撇嘴就哭了,抹着小脸一扭一扭的,慢慢走了。梅梅眼窝一热,快步追过去,从身后搂住他,说孩子,吃饱了么?男孩点点头。一块钱有点少吧?男孩这才转过身子,仰起小脸,闪着一双乌莹莹的大眼睛,说姨,俺想攒一大包钱,出远门,到最远最大的树林子去找俺姐。她抓住男孩的手说,走,跟阿姨去一下单位。
单位下午要做一期道德讲堂,梅梅想利用这次机会,号召职工给男孩捐点钱。她先找宣传股。股长听了也是满脸的凄风,满眼的苦雨,边蹙着眉整理桌上的学习笔记、政治笔记和业务笔记,边递过来一百块钱,说,讲堂内容都是提前定下的,局长不点头,咱也不敢加上去。又去局长那。局长听完,从老板椅上挺直了身子,一颗蒹葭苍苍的头颅直冲着顶灯,不由自主地摇摇,又摇摇,直摇得满室芦花,四下里飘霜。然后颤颤地掏出二百块钱,按在老板桌油光乌亮的桌面上,慢慢推向她,仿佛纸币上压着沉沉的石头。局长说,给那个孩子吧。党组定下的事,我也不便改,下次,嗯下次。梅梅只得退出来,在走廊里碰上税收一股的昆妹。她一说,昆妹便嚷开了。哎呀我说梅姐,你是元谋猿人吗?现在农村可劲儿生孩子,孩子大了就放出去要钱、碰瓷、偷盗,报纸上登得铺天盖地,家里的洋楼一座一座的。快回办公室看看吧我的作家姐,包里的钱物别叫他卷跑了,才叫个排场。
包里倒没啥钱物,只有桌子上放个新买的文具盒。盒面是绿色亭亭的荷叶,欲放未放的白莲,很美,很好看。上面配有几行美体小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盒里放二百块钱,准备在讲堂上送给困难职工,算是一点心意。梅梅不相信男孩会那样,又到税收二股磨蹭一会儿,才回到办公室。哪成想,进门打眼一扫,文具盒真就不见了,她自然要恼了。
梅梅把文具盒放进抽屉,想想,又掏出来,慢慢打开盒盖。只一眼,心就腾地一下炸成了一把油麻花。满满一盒都是一毛五毛的纸币,用线绳和皮筋扎着,紧紧码在一起,并没有两张百元红色大钞。把那些小钱磕在桌上,划拉开,还是没有,梅梅的汗就下来了。
捣鼓啥呢?脚没迈进门,昆妹的公鹅嗓子就裹着一阵风,似一只鹅头拧着个长脖子钻进了屋。见她在那里愣怔,昆妹把手里拿着的文具盒朝桌上一拍,说看你急的,没丢,俺家小妮子看着漂亮,就拿我那了。刚刚才瞅见里面还有二百块钱,我说不管,得给你梅姨送去。不然,她又得拾掇你黑叔满世界扒拉着找了。
2
中午梅梅没回家,下了班直接走进小吃一条街,开始寻找男孩。她觉得一刻不将文具盒还回去,她的愧疚就像一只大毛虫,一刻不停地会用满身毒刺刺着她。
小吃街中午还好,多是上班族来吃,推杯换盏吆五喝六的少,不闹,都是简简单单,吃饱走人。梅梅走走停停,不在意摊主揽客的招呼,只把目光一网网撒向左右两边摊位,生怕漏掉了目标。
走着走着,只听前面一个童声喊道,爷爷,钱。梅梅抬眼望去,见是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站在条形砖砌成的灰色人行道上,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正回望着笑眯眯的爷爷,不知道该不该去捡那张满面红光的一百块钱。爷爷扭头朝两边扫扫,喊道,谁的一百块钱掉地上了?食客们有的摸兜,有的摇头,有的摆手,大都面无表情地眨一下眼皮,没人吱声。爷爷说,宝宝,拾起来吧。男孩嗯一声,正待去捡,斜刺里插进一个脑门倍儿亮的男人,一把抓起那张钱,左手甩着掌,右手攥成一只拳头,挺着腰杆子就走了。食客们看到这一幕,该吃吃,该喝喝,大都面无表情地瞭一下眼皮,还是没人吱声。男孩愣住了,就那么弯着腰,撅着小屁股,依然保持那个捡钱的姿势。
看到这一幕,梅梅惊得大张着嘴巴,仿佛有半截筷子撑在嘴里,难受得伸长脖子,一声都挤不出来。依着性子,她真想几步跨上前,劈手揪住那人荡在胸脯子上的猪尾巴领带,质问他一个大男人,咋有脸去跟孩子抢钱!想想现在的人,她只有摇头叹气的份,一句话都懒得说。难怪昆妹常常会气得跺脚,捋起袖子,两只熊掌似的大肥手拍得啪啪响,你你你,俺姐耶!
也是,自从调入新单位后,梅梅如一支“在娘家青枝绿叶”的青竹,陡然间变成了“到婆家骨瘦皮黄”的竹篙。刚开始,局长在晨会结束时宣布,中层以上干部留下,继续开会。她愣了下神,想留下,因为多年前她就是领导层了。想想自己刚调来,职务没明确,还是用鞋底滋拉滋拉蹭着地面挪出了会议室。
后来,与她一同调入这个系统的省厅明处长来调研,她心里竟然萌生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倚在办公室的门框上,一分分、一秒秒等待一次直接走进会议室的机会。但那扇门,像是一块铆死的钢板,就那么固执地关着。梅梅本想任性一次,踮着脚尖旋开门,探进半个身子跟老领导摆个手,或者点个头,或者一笑,或者就是眼光的一个交集也行。但梅梅不任性,除了黑脸差子,她从来就没任过性。不料,次日早上明处就把电话打来了。他说梅局长,你不够意思呀,怎么不来看我?梅梅心里一热,说老领导,我现在不是副局长了,偎不上去啊。明处唉一声,我说我与梅梅是多年的老同事了,也是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她现在怎么安排的呀?他们说你现在搞党务。我说她分管的业务曾是我们全省的一面旗帜,现在搞党务嘛,也好。中午叫梅局过来,陪我吃顿饭吧。他们说你忙着呢。晚上我说,一晃几年没见面了,叫梅局过来打打牌,叙叙旧吧。他们又说你没有时间。我心里透亮儿,现在的梅梅,哪有那么忙?
前不久,在昆妹鼓动下,梅梅专程跑了趟省城。人事处长听了她的简述,倒杯水递过来,梅梅慌忙躬起身子,双手接住。处长说,你这个事情啊,还真是没法办。一呢,我们没有领导职数;二呢,省编办不给追加;三一个,你也没有从原单位带来。所以,嗯,请你理解。处长语调不高,声音雨丝一样温润。脸上的线条也很细腻、柔顺,似被春风刚刚拂过的垂柳。两只小眼睛只留下一条断开的细线,盈盈地在灯光下闪着笑意。但梅梅还是鼻子一酸,眼眶里涌出泪来。为了掩饰,赶忙低下头拿手绢捂了上去。处长走到她身后,轻轻拍两下,手就抚在了她的后背上。
想着这些烦心事,瞅着大汤锅里咕咕嘟嘟冒出来的热气,都中午十二点多了,梅梅居然一点食欲也没有。她懊恼,愧疚,真不应该对早上那个可怜的孩子“有罪推定”,非让人交出与自己那只一模一样的文具盒来。他手里没有一分钱,也不知这时候要到吃的没有。正兀自出神时,只觉一辆电动自行车吱的一声冲到身后,前轮刚好抵在她的腿弯上。梅梅身子一软,慌忙侧身退出一步,边拍腿弯上的灰边说,你慢点啊,差点轧着我。骑车女孩杏眼一瞪,按喇叭也不让道,我看你是成心找轧!梅梅气得脸腊黄,指着她说,你,你,咋这样说话。那女孩骑在车上,一弯车头,甩下一句话,老女人,找老男人轧吧,而后嗖的一下飞远了。
梅梅一口气堵住嗓子,憋得直翻白眼,像只呆鹅愣在街边。早摊点女老板拎瓶陈醋匆匆走过来,一碰她胳膊轻声劝道,白气了,现在人都这样,犯不上。白是土语,是别和不要的意思。她这才苦笑一下,回过神来。按按心窝子,呼出一口长气,跟上去几步,问女老板,可看见早上那个要饭的孩子么?女老板问,咋了?她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女老板听后告诉她,现在人都这样,吃个熊饭穷讲究,见个要饭的进门,又捶桌子又瞪眼,说是看着腌臜,吃不下饭。大小摊点为了留住客人,见了要饭的恨不得用剔骨刀砍,用滚锅油泼。只有俺可怜那孩子,同意他早餐搁这地场要一个饭时,中午晚上就不管来了。梅梅沉吟一会儿,说他中午会到哪个小区要饭呢?女老板用眼梢子睃睃她,小区有保安,连条狗都混不进去,白说是个小要饭的。再说了,就是没有保安,就算不到小区,哪个不是进家就哐啷一声关上门,打猫眼里朝门外一瞄,不是熟人,任你把嗓子喊成破锣,也不会开一丝门缝,扔一块凉馍给你。梅梅有些急,那孩子,难不成要到机关去要饭?女老板哼哼一笑,那是他去的地场吗?有一次俺去买菜,半道上突然想拉稀,捂着肚子跑进一个单位,叫二逼门卫连扯带拽给搡了出来,说是办公重地,哪是外人想拉就拉的,害得俺差一候候就屙裤裆了。说到这儿,女老板侧过身子,抖着两只满肉的胸,脸上的笑显得比县长还懂政治。现在人都这样,犯不上。你最好去车站那地场转转,兴许能碰上。
3
花溪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时候,却在要求家家户户养老鳖,力争三年内把花溪变成老鳖县;别人为招商引资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却在举全县之力,进京赴省,铺天盖地宣传牛鞭的养生保健功效,力争三年内把花溪变成牛鞭县;国五条、国八条出台,严格控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势头的时候,才想起来去搞土地财政,卖地,建房,拓展城市空间,力争三年内把花溪变成皖北新城。所以这地方至今没有像样的工业,很穷。但穷有穷的好,天蓝,水碧,满塘的清莲,空气新鲜得似十五六岁少女的鼻息。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花溪贩鱼,买羊,整车整车运土鸡。加上东西薅着蚌埠、阜阳,南北摁着淮南、亳州,所以这个小小的花溪车站,一年到头就没分过淡旺季,车哗哗地流,人嗡嗡地拥,甚为热闹。
候车大厅闹闹哄哄,张扬着男人的汗、女人的肉和苍蝇的腿。男人女人如超级蜂巢上的蜜蜂,在那里拱来拱去。梅梅皱起眉头,除了吸进满鼻子满肺浓汤似的方便面味、卤菜味、馊饭味、烟酒味、大蒜味、臭豆腐味和闷屁味,就是感觉有木棍一样的胳膊在正面朝乳房上顶一下,有热烘烘的手在背后往屁股上抹一把,连那个男孩的影子都没瞅见。急急忙忙挤一圈,感觉像陷进黏糊糊的柿子林里,就憋足了气,闷头顶出大厅门外。她想找个视线开阔的地儿歇歇,顺便又能盯住进出的人流,左顾顾、右盼盼,门外小吃点、水果摊、烧烤架、书报亭,一处挨着一处,还真是寻不着一个敞亮的歇脚点儿。
正东张西望着,一只马扎连着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同时从身后递过来,阿姨,找人的吧,先坐这歇会儿哈。梅梅低头一看,见是一个女孩,怀抱一把二胡,裹着满嘴的饭菜,眯着两条肉鼓鼓的小眼正朝她笑着。梅梅点点头,忙回她一个笑,弯腰坐在了马扎上。马扎有点小,梅梅的屁股有点大,压得马扎吱吱响。女孩瞟瞟她满溢在外的屁股,歪着头斜斜地又是一笑,阿姨是巧长,该大的地方大得真是性感。梅梅摇摇头,嘿,都四十四五了,哪还有性感。女孩瞟瞟她脸上身上,说阿姨,人跟人真是没得比。你看我吧,眼小成了一条缝,胸瘪成了两张皮,屁股瘦得不分瓣,该大的一个都不大。脸呢,横着堆肉,就是不朝小了长,像一只圆鼓鼓的老倭瓜。所以怀礼爹买下我转天就大呼冤枉,说他三万八千块钱买个破烂货,后来就掐着拧着叫俺出去勾引邻村的老光棍。梅梅一听坐直了腰,你这孩子,是被人拐卖了呀。女孩说,嗯,十四岁那年在花溪中学桃园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叫五岁的小弟蹲桃树根前瞧蚂蚁上树,不准乱跑,自己出去要点钱、讨点吃的。碰上一个大姐,说她今天十八岁生日,心情好,让我上她的车,开车回家给我拿吃剩下的蛋糕和饮料。车子七扭八拐,把我推到另一辆车里。俩男人,一个捏乳房,一个掏裆,可把俺给折腾哕了。后来,七联系、八捣鼓,把我卖给了戏班子。梅梅惊道,我找的小男孩,说不定就是你弟弟。女孩肉眼泡一睁,是俺弟?梅梅讲,对对,他讲过,姐姐让他等,不准乱跑。女孩伸把抓住她,阿姨,一准是俺弟,他在哪?梅梅苦下脸,掏出文具盒,我错怪了他,到现在都没找见,这个也无法还给他。女孩接过文具盒,摸摸绿色的荷叶,抚抚清清的白莲,低声赞道,真美,是俺弟的,太漂亮了。而后把文具盒搂在怀里,仿佛搂着自己的亲小弟。梅梅就势抓住女孩的手,说孩子,他肯定是你弟弟,我一定能找到他。女孩肉眼泡一红,佝下了腰,长长的披肩发如戏台上落下的幕布,挡住了那张暄腾腾的蒸馍脸。好一会儿,她才扬起头,一甩长发,谢谢阿姨,找到请一定送来,我就在这地场等,白天,夜黑,都不挪窝。梅梅点点头,嗯,一定。接着又问,那,后来呢?女孩咽口吐沫,揉揉眼泡说,后来,老板嫌我肉没有肉,样没有样,就转手又把我卖给了怀礼爹。梅梅说,报警呀。女孩拿小拇指剔剔牙缝里的残菜,说盯得紧,直到给他生下怀礼才算准许我出门,再报警,警察抓了他,怀礼就没爹了。梅梅唉一声,可,可是,那就跑呀。跑啥?女孩直视着她,声音抖抖的,像眼眶里欲落未落的泪花,说我跑了,他一准满世界撵。豆虫大的怀礼,独个儿躺在一整床烂棉花套子里,不就像俺和小弟一样,成了无人敢沾的孤儿了。梅梅疑惑地看看她,那你现在?就我这样该大不大、该小不小的女人,谁稀罕?三天都摊不上一个,而且价钱也贱,多的十块二十,少的只拍给你三块五块,有的甚至除了一只大裤衩子,就剩下一条光想着打洞的肉头虫。都是光棍汉,衣兜里都很瘪,碰上提裤子走人的,俺也只有自认倒霉。怀礼爹赖我不卖力、赚钱少,就扎脚心、烧大腿,折磨急了,俺就拎把二胡偷跑出来了,叫他在家作作难,就便也找找失散几年的小弟。
梅梅看着这个苦命女孩,鼻腔酸酸的,一时竟也无语。想想自己,生在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穿金戴银谈不上,衣食无忧倒是真的。大学期间她是公认的校花,小鼻子小嘴小眼睛,精巧地配置在那张巴掌大的小脸上,显得格外洋气。她高挑的个儿,一截葱白似的大长脖子,溜溜的肩,大大的臀,曲线优美得哪怕裹一身厚厚的冬衣,都掩不住那种一步三颤的诱惑。追她的人,萝卜白菜豆角子,归成堆,得有堆尖一团筐。特别是本市同学,那个短腿极为烧包地向两边撇着,肚子极为正统地向正前方盘着的吴莱,专捡餐厅、课堂、寝室里这些人多的地方献殷勤,声称在梅梅面前咱啥也不是,最多算是一只癞蛤蟆吧。但咱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有能耐一口吞下她这只白天鹅,咋的?爸妈对这个夸下海口的癞蛤蟆还是很上心的,说他家住在县领导专住的小红楼别墅群里,一层大院子,接二连三的几茬保姆都能安排进有钱、有权、管事的这个局那个局。你嫁进去,虽不是旧时的王府相府,但在花溪这片针鼻大的小地方,能从红楼大院里进进出出,那本身就是档次哪。梅梅的马奇诺防线眼看就要被德意志帝国的梅塞施米特-飞机炸开时,癞蛤蟆陪他爸来了趟梅家,梅梅一看爸爸塌着腰、妈妈堆着笑的那副下作样儿,吧哒一声闭上门,羞恼得再也不肯走出闺房半步,坚决断了这条线。
后来,因为经常往返于大学和家里,几次打车结识了黑脸差子。第一次打车他没收费。他说不收钱,俺心里得劲;收下钱,俺就堵得慌。梅梅看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吭吭哧哧黑脸胀成了狗头枣,心一软把钱就又放回了小皮夹。第二次打车他也没收费。梅梅给她钱,他头都不敢抬,就那样单手扶住车门,一旋一旋地磨鞋底,似乎鞋底子就是一把锈了千年万年的刀,不那样磨,就没法割肉、利馍、切面条。第三次打车他还是没收费,只是闷头从后备箱里卸东西,然后伸出莆扇似的左右手,一手几大件,扑踏扑踏拎上高高的五层楼。梅梅看他黑脸被汗水油漆得宛若亮闪闪刚出锅的糖炒栗子,想反手把门一关的心倏忽一松,就让他进了门,并从贴身衣兜里抽出一张面巾纸递给他。他没去擦汗,就那么嘿嘿傻笑着握在手里。梅梅也热了,又抽出一张,贴贴额头,搌搌两腮和嘴唇,随手丢进门口的撮灰斗里。送他出门时,梅梅的目光无意间从灰斗划过,发现刚丢进去的面巾纸不见了,用眼角的余光一瞟,见他把那张从撮灰斗里将将捡起来的纸,暗暗捋直了,与自己手里的那张,轻轻叠在一处,紧紧攥进手心里。梅梅心头一颤,虽然唇线抿得被强力胶粘了一般,但那个心呀,早就薄如他手心里的纸,有了一种窒息而死的感觉。整张脸上,陡然间撒满了三月的桃花瓣儿。事后梅梅倚在门上、伏在书上、躺在棉软软水柔柔的床上,迎着朝霞想、伴着落日想、数着星星想,愣是想不起来他是如何走的。耳畔里除了他扑踏扑踏下楼的声音,就是自己怦怦心跳的声音,还有满面桃花在双腮摇摇曳曳的声音。当她宣布要嫁给黑脸差子时,妈哭得无声无息,弓着脊背,耸着肩膀只是抽。半晌天,妈才说,你傻呀!
婚后不到三年,妈妈的话,她就领教了。地方上处处结满吴家的网,官场上沾亲带故的,数一数、排一排,也几乎全是他家的人。梅梅守着黑熊似的黑脸差子,虽然不曾后悔,虽然紧着牙过她的酱豆就大馍的日子,虽然因为工作成绩加机缘巧合提了个副局长,但生活和工作的艰难却让她深受教育。后来业务划转,她毅然脱离地方,跳到现今这个垂直管理的新单位。哪料到,这一跳,竟然将自己二十年加班加点熬来的一顶官帽给跳没了。
想到此处,梅梅脸上也是阴云密布,说不上来的惨淡。看一下手表,她说我再转转吧,看能不能找到你弟弟。女孩起身一笑,送她离去。
梅梅把车站附近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都走了一遍,没有找到男孩,一看时间,赶紧转到十字路口,准备打车回单位参加道德讲堂。正张眼乱瞅着,忽听不远处一阵哄乱。趋前一瞧,见一个脑门倍儿亮的男人双手撕着女孩的长发,死命地朝候车大厅里拽。女孩边往后秃噜边哭,不回,打死俺也不回,骨节暴突的腰身比一条落水的柴狗还要瘦。亮脑门腰背一拧,猛然将女孩掼倒在地,腾地一脚踢开挡道的二胡,抓起马扎,劈头盖脸向女孩砸去。一看那个腰背,梅梅印象太深了,几乎叫出声,这人,就是插进去捡钱的那个亮脑门儿。人群一阵骚动,不住地有人嘀咕一句,淌血了,淌血了,却都袖着手、冷着脸,没有一个上前拉架的。正在这时,半截粗壮的黑木桩子戳进人群,如一枚木工的巨形楔子几步楔入圈内,拎起亮脑门儿,反手一抖,将他送出两米开外。梅梅眼前一亮,是黑脸差子。亮脑门儿稍一站稳,身子随即朝上耸了几耸,挺起腰杆子说,我说爷们儿,恁可白来找事!黑脸差子抓起马扎,屈起右膝,咔嚓一嗑,整只马扎七零八落,断作几截。然后黑脸一板,咋了,我找事你能咋的?见此光景,亮脑门儿立马矮下身子,换上一副笑脸,耸起肩说道,对不起大哥,俺讲话有点冲嗬。然后掏出烟,弹出一支往上递,被黑脸差子一抬手挡了回去。他嘿嘿一笑,大哥,这娘们儿是俺女人,儿子才一岁多一点,狠心扔家里一个人跑出去浪,一浪就是恁些天。俺叫她别浪了,回家吧,还敢犟嘴,嚷着打死也不回。大哥你说不打,她不骑鼻子上脸屙俺一嘴呀。黑脸差子仍没放脸,伸手一扯,又将他扯到女孩身边,一指地下,你看看,有这样打老婆的吗,你是想要人命呀?说着,从裤兜里一张一张,捻出三张钱来,看了看,甩手扔到亮脑门怀里,这是五十块钱,赔你马扎,剩下的去给老婆买碗汤喝。说罢返身就走,声音嗡嗡的,又送回来一句话,打老婆,算个什么鸡巴男人。
黑脸差子的话,引来一阵哄笑。梅梅没有笑,却在笑声里红了眼圈,酸了鼻腔,巴掌小脸上先是云消雾散,接着冒出两条小溪,随即便是百川齐下,清丽爽亮得分不清哪是泪光,哪是霞光了。
4
下午的道德讲堂如期进行,先进工作者抱病加班、不顾病妻的先进事迹,支持丈夫工作、侍候瘫痪公婆的身边好人,引得全场一片唏嘘。赶上局长发表重要讲话时,昆妹抱起一摞文具盒,蹬蹬蹬,突然几个大步踏上大讲台。她敞开摇滚歌手才有的“重金属”嗓门儿,借着麦克风的放大威势,震得会议室仿佛开进了一辆一百八十八吨重的鼠式坦克。她说有个要饭的小男孩,是梅姐的朋友,需要一只文具盒。这是我买的,一共十个,请帮帮梅姐,帮帮我,找到那个小男孩,送给他,并捐助二百块钱。说罢,从紧绷绷的屁兜里,掏出两张红彤彤的百元纸币,啪的一声盖进文具盒里。然后一抱拳、一鞠躬,高腿阔步,蹬蹬蹬,几步又回到坐位上。职工们对这种横插一杠子的做法很不适应,愣了一下神,静了一下场,偷觑一眼局长,见他摇着一颗蒹葭苍苍的头颅,看不出脸上的红,也看不出脸上的白,先是一两个,再是三五个,而后便轰的一下拥上了台。拿到文具盒的,仿佛犯了错误,眼神藏藏掖掖,几乎全都低着头、踮着脚,不声不响潜回了坐位。没拿到的,反倒像母驴群里的一头大公驴,一副别人雌伏、唯我雄起的模样,昂首挺胸、闹闹嚷嚷,目光如鬼子炮楼的探照灯,漫无边际地扫来扫去,有的居然还敢在局长似睡非睡的脸上狂扫了几通,定光了几次。
晚上,黑脸差子匆匆赶回家,习惯性地拎瓶开水就朝外走。梅梅说,回来,今个不跑了。黑脸差子点住脚,依然保持着前倾的身姿,说不跑车哪管,我是男人,得挣钱呀。她说,不跑了。黑脸差子笑笑,迟疑了一下,立直了身子,闺女刚上大学,正等用钱呢。她多了俩字,我说,不跑了。黑脸差子黑塔似的身板,顷刻化作柔弱的依依杨柳。那就早回,你看十点行吧?她站起身来,双手往胸前一抱,放慢了语速,我说不跑,就是不跑。黑脸差子转过身来,发现她那两只不是很大的眼睛里,已经涨起了钱塘潮,涌动着一波强似一波的春水,不觉也变了声,我儿,爸听你的,你说不跑就不跑。黑脸差子一激动,就这个腔调。
饭是黑脸差子做的,碗是黑脸差子盛的,锅是黑脸差子刷的。这一通忙好后,又削了一只红富士,切成橘瓣大的小牙,插上两根牙签,盛在一个白瓷小盘里,端了过来。
梅梅斜卧在三人沙发上,一张小脸被灯光一照,似故宫博物院珍藏千年的定窑白瓷,肤质柔腻,肤色奶白,静静的,散发着一种禅意的、神性的美。黑脸差子一时失了神,盘中的果瓣斜滑到盘沿了,也没有察觉。梅梅喊一声,苹果。黑脸差子,嗯。梅梅又喊一声,快,掉了。黑脸差子又是,嗯。梅梅一伸手,你这个黑脸差子,给我,马上就掉了。黑脸差子还是一个嗯,嗯过了一低头,方才醒过神来,忙端正了盘子,俯下身子,梅局长,请吃苹果。梅梅一听,伸出的手又转了向,朝黑脸差子脸上抹了一把,傻了吧,刚才嗯啊嗯的,现在又喊我局长,当真神经了,不知道你老婆现在不当副局长了啊。黑脸差子就势坐下来,让自个变成沙发扶手,把她的头挪到自己热乎乎的肚子上,说我儿,这么多年爸听人喊你梅局长梅局长,心想能录下来刻成光盘就好了。咱就关上窗子,把音量调到将将好,乘没有客人的时候在车上放,晴天听,雨天听,听得每条道上的交通指示灯,红脸绿脸都知道,俺老婆是谁?梅,局,长。现在没人喊了,俺就想,没人喊俺喊:梅局长喝茶,梅局长吃饭,梅局长空调爸给你打开了,去书房写大部头书去吧。梅梅坐了起来,白他一眼,黑脸差子。黑脸差子笑了,嘿嘿。梅梅说,我找你,原本没想着走官道。后来侥幸得了顶官帽,也没当作个一根大葱半头蒜。可是当今社会就是这样啊,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三六九等。譬如前几天推荐干部,机关里二十几个人,却要分发出红黄白三种表格。黑脸差子不解,啥红黄白?红表是局领导填的,黄表是中层干部填的,白表科员填的。靠,一个鸟事,搞出几种鸟毛,真他妈改革开放。梅梅正色道,什么几种鸟毛,这就是等级,这就是身份和价值定位,懂吗?黑脸差子点点头,嗯。嗯过了看她撇一下嘴角,现出不甚满意的神情,又忙着补充,懂,俺懂,就是客人嘴头子上叨叨的正乡级副乡级,正村级副村级,还有啥子公务员、事业编,对吧老婆?对。梅局长,你填啥表?梅梅朝沙发上一靠,从小腹经胸腔,从胸腔再经口腔,这才缓缓吁出一口气来,啥表?你老婆现在是——白表。黑脸差子大腿一拍,放屁,红表,红表才对。她说,是呀,所以我心里那个堵啊。黑脸差子腾的从沙发上跳起,妈的,老子明个印一捆子红纸,印一捆子红表,让俺女人在家里用红纸写书,到单位用红表填表,白理他个红黄白!说罢转进厨房,旋即端出一盆温水,给她拿开拖鞋,脱掉袜子,轻轻挽起裤腿,捏起两只白藕似的脚慢慢浸入水中,白堵了啊,爸给你洗脚。我儿,咱,睡觉。
那一夜,黑脸差子的宝贝威风八面,霸气得让她全身的钙质流失净尽,整个人儿,恰似一盆醒了又醒的发面,满满的柔软,满满的酵香。梅梅黏在黑脸差子怀里,把连续多日欠缺的睡眠,一股脑地黏了回来。次日晨起做早饭时她才想起,夜里还做了一个梦,她找到了男孩,送还了他的文具盒。女孩搂着她的小弟,那个哭啊,那个笑啊!送文具盒的有昆妹,有黑脸差子,有守纪律、讲规矩的同事们,还有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收到文具盒的不只这个男孩,还有几个,全都咧嘴笑着,露出各具特点的小豁牙。
梅梅不由自主也笑了,小小的眼睛笑成了两只水灵灵的嫩豆荚。她推开厨房的窗子,痴痴地朝东方的天际望去,此时的太阳已经破茧而出,用初生婴儿般的笑脸,将东天涂抹出一片梦幻般的玫红与橘黄。晨风丝丝缕缕飘进厨房,清新,凉爽,梅梅深深吸进一口气,兀自又笑了。她发现自己真是一块当作家的天然材料,都十一月中旬了,不仅能嗅出荷叶的青气和荷花的馨香,还能感受到晨光带来的暖意,入心入肺的在氤氲,在蒸腾。
昭明文学奖
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cs/86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