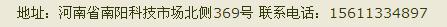海子我在思考真正的诗歌
在这里,我们坚持道义,回归本质,致力于中国原创诗歌的严肃蓝本
也夫,男,年生于山东,中国当代行为艺术家、诗人与牧师,现居北京。也夫先生是国内具有丰厚学识的谦抑型诗人,主张诗作以神(天道)的视角俯瞰大地苍生,让灵魂运行在地上,其诗质朴而有分量,情感殷实又满含恩慈,同他的行为艺术作品一样受到国内外媒体和艺术家的
26日是诗人海子的祭日,处于感情原因,我还是决定提前2日为诗人海子写下这篇文章,以作怀念。尽管海子的走掉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但当我在十八年后的这个春天,一个人独处在这间小囚室里的时候,我依然想起海子所写下的一句让人心潮澎湃的诗歌:“春暖花开,面朝大海”。
01年的今天,我和诗人西川初次见面并认识,那是在大山子南湖渠桥旁边的老中央美院,西川三楼的办公室里,那次我们有过两小时的交谈,谈起中国当代文学和诗歌来,并谈起了海子、骆一禾、和戈麦。26日,西川处于老朋友的感情原因,没有去北大参加未名诗歌节,而我一个人去了北大。其实谈起海子,从很多年前,西川、骆一禾、王家新等都写过关于海子的文章同时回忆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生活。我来写海子,实为后者叙聊而已。
由于我近期写了一些关于“文学与艺术的陷阱”的文章,以及作了一些符号学方面的文章探讨,就想着抽出时间来写写海子,写写一些关于国内诗歌的状况;前不久很多外地的更年轻的诗人,经常和我探讨诗歌写作方面的问题,每次我都搪塞过去,回避我的诗人身份和我的诗歌,大家只是喝喝酒瞎聊而过,因为我个人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个诗人,也没写出什么出色的诗歌,并且知道写作快乐中间伴随的压抑与痛苦,所以我一直不喜欢在生活中探讨太多关于诗歌方面的话题,所以很多时候也显得不太负责任;总想着和别人说,诗歌能不写时就不写,但是话说回来,写诗是天性,不是偶然的,谁又能阻挡那些诗人和有诗歌抱负的人对诗歌的书写与通过诗歌表达的欲望呢?所以只好大家都沉默的各自努力吧。况且,写诗是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今天网略很发达,交流和通过网略发表自己的诗歌也很容易,所以现在诗人很多,诗歌也到处是,而我却看的越来越少,所看的书也翻来覆去的就那几本;其实也不敢和大家纯粹交流关于诗歌的问题。我所能谈的不过是我个人一点局限的想法和看法而已。
基本说来,诗歌算是年轻人的事业,因为诗歌同时是寂寞者的事业,所以写诗的那部分年轻人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寂寞者。由于寂寞,诗人就想找点事情去做,去琢磨东西以打发掉那些让人觉得寂寞的时光,由于琢磨就容易陷入自身的孤独,由于得到孤独的营养,于是就又开始书写,由于诗人们真正进入了书写,所以他自身意味着将从人群中抽纱而出,回到孤独旁边不得不以孤独厮守为伴。海子从进入昌平正是如此;他度过了他的最为孤独的一段岁月。正因为他的让人无法想象的那份孤独,成就了他的庞大精神质量建构的诗篇。海子和诗人骆一禾、戈麦一样,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基本成为青春写作的代表诗人;他们的诗歌基本九十年代初才全面面世,西川为海子整理了诗歌,张玞为骆一禾整理了诗歌,西渡为戈麦整理了诗歌,所以他们的诗歌基本影响着九十年代的一批诗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短命并在诗歌上挥发掉了自己整个的青春,海子的诗歌从阴性走向阳性,在他最初的短诗抒情中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悲伤色彩,并显出强烈的文化情结和对纯粹干净生活的渴望,也许后人说他由于写诗而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但从他的诗歌中却充分透露出质朴生活色彩和人间粮食的味道;在他的短诗《亚洲铜》、《女孩子》、《日记》、《山坡上的四姐妹》以及长诗某些段落中,都能看出此点;他在搜集与整理民歌的同时,并将他儿时玩过的游戏以文字方式纳入了他的诗歌中,可以猜想那游戏在他的生命回忆里的重要性。因为海子15岁就离开安徽农村进入了北大,他的童年到少年在家乡度过的时光非常少,所能让他回忆的肯定是相当珍贵的,也是仅有的一点奢侈的儿时生活。由于他过早的涉入成人世界,在处理感情上尤其男女感情上,我猜想肯定不是那么成熟与到位,这正好给他提供了很多幻想的机会,可这种机会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与坚硬来说,同时给他感情生活制造了实实在在的麻烦;由于这种麻烦存在和没有正确处理的手段,就意味着有危险降临。所以他在昌平所能依恋的大概只有他的诗歌。从他的短诗到长诗的发展,就能看出他的感情与精神的变化过程。他的希望就开始走向长诗的思考与书写,并转向阳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思考真正的诗歌”,我想,假如没有这种诗歌上的阳性转变,他本人在诗歌上不会走的那么远,也许早就到了某种尽头,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然而,在他的《太阳七部书》中,我们同时能看到作为诗人海子的另一种“野蛮”,正是这种“野蛮”支撑他的诗歌书写与语言探讨上走的更深远;我们从他长诗的命名上就能看出此点来,如:他对长诗的命名:“弑”、“弥塞亚”、“土地-断头篇”等。这份“野蛮”同时表现在他的大部分长诗中。他似乎是在但丁的“地狱与炼狱”中挣扎了到底,最后一点点慢慢靠近天堂那微小的亮孔的。自从他看到那亮光,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直抵那耀眼的辉煌;于是他把自己称为“太阳之子”,引火烧炼自身。完成了他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任务与情结。也许,我们可以料想海子是走的另一条路,即:一直随陷阱或说黑洞的旋转沉落与那黑暗的中心,并在深渊的端点也即临界点上洞悉了那光,就是说他是向着黑暗朝里朝下走的,一直走到了黑暗的尽头,而不是背着黑暗向上走的;虽然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因为从他长诗的书写速度和质量庞大上也能看出此点。稍后回来探讨此点。
现在我们以海子为参照来对比一下骆一禾与戈麦。也许在诗歌写作尤其长诗写作上,骆一禾是最懂海子的人,所以他在后来纪念海子的文章《我心中的海子》中,写道:“海子的诗歌不仅对以前、现在、甚至将来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在他们三人的短诗写作中,对真实生活、女人与大地之物的书写,应该说戈麦写的最好,精神与思考最凝聚,因为戈麦写出了那些东西与诗歌本身的可能性。而海子重在旁观以俯视的姿态,去包容并衍生于那些东西;戈麦在诗歌中离那些东西走的最近,当然在现实中与女人不一定距离是近的;骆一禾则以哲学性反思而渴望着与那些东西的真实距离的拉近。然而骆一禾的幸运是他自觉的走向了他个人的长诗思考与书写之路,他和海子的区别是:他的诗歌走向了阴性。我们从骆一禾的长诗中就能明确的看到此点;他走向了大海的深渊,以“赤潮”、“黑潮”为精神意象在搏斗中书写;所以,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很难看到像海子诗歌中那种荒原、沙漠之感以及对麦田、石头、箭壶、马等物的描写,海子即使在夜歌中也反应如此。而骆一禾短诗中经常写到“北方的大平原”,但到长诗部分就被卷进了海的深渊里,于是他渴望的是光明,是人类可视的“血”,他把海浪称为“赤潮”,而“血”的意象正巧对应了他现实的病症和死亡,因为骆一禾由于脑溢血的病症而走掉。这或许是他的宿命,只是反过头来以诗歌暗示与证明罢了;因此,骆一禾的诗歌正是他自身的寓言。骆一禾着重写海的原因,我猜测,在他们三位诗人当中,他是唯一真正品尝到女人滋味的人,因为只有他已经结了婚;而海子与戈麦却处在可望而又不可及的状态,他们二人与女人真正保持着距离;这一点从他们的表现上就能看出。海子在幻想中屡屡把女人写成复数,不断从大的形上写女性,以致成了他的理想与精神关怀;对女人的全部细节来说,海子基本是个旁观者;戈麦则屡屡隐秘地写到一个“薇”字,写他所能看到的女人的胸怀,并与大地之物相类比与转喻;骆一禾则经常直截了当的写女人,他写到女人的手时,说:“……那只手,……握过我阴茎的手……。”因此,我猜测不错的话,骆一禾长诗追逐到“海”的内容,实有女人的关系。
然而,戈麦的诗歌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他以这种可能性寓言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他的诗歌中布满了现代派文学作品灰色调的影子,对于戈麦来说,他本人连同他的诗歌都是灰暗的,比现实更灰暗的灰暗。所以他本人没有进入到长诗的写作就被灰暗击溃了,他所希望要的正类似于骆一禾所要的那种光,一种他个人方式的湿润感,将自身囊裹与内;戈麦没有得到海子的那种辉煌,也没得到骆一禾在更大黑暗与湿润里临近的那“血”的光,于是他选择了大地上他所能最近距离靠近的“水”,他最终将并没进行完的生命撒手投进了北京西郊的万泉河。相对与海子与骆一禾来说,戈麦是阴性与阳性的中间临界点,他倾心 然而,按着这条路分析的话,海子与但丁就成了同路好友,相携而进,或者说但丁扮演了他的引领者(维吉尔)的身份,引领并期待海子同诗友们的到来。但丁的伟大之处是,将他的《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都写的一样辉煌;而诗人海子从他的第一首诗歌《亚洲铜》就开始奔向了那种辉煌之路,同样将他的短诗与长诗一样写出了辉煌。我为诗人海子感到幸福,同时为骆一禾与戈麦感到同样的幸福!
握三位诗人的手!
……。
.3.24于北京
(本篇评论文章经作者独家授权《赤潮诗社》首发,严禁转载他用!)
-end-
投稿邮箱:
qq.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dzz/98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