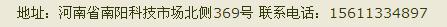诗话文章隅山主人诗歌杂谈在路上
诗歌杂谈:在路上
隅山主人
1、由于寻找本民族文脉的文化倾向,当代诗的精神会在很大程度上向古典诗靠拢。一个新的植根(或融合)中国古典思想的哲学系统会诞生。(这方面安乐哲,郝大维,成中英,杜维明,余英时,李泽厚,刘小枫,赵汀阳等等一批研究者,可以说是在尝试建立一种文艺复兴式的核心系统)新诗和古诗会共同享用这个系统,从而在语言上互相渗透,找到“中国式的表达方式”,使古今诗歌之间互相构成一条完整的诗歌链。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诗成熟,与古诗的语言精神产生断裂,大概化了二三十年,那么这个回归或衔接的过程应该会少于二三十年。
当然,这不是意味着纯粹的古典或西化诗歌,不再留存,而是不再大行其道,成为所谓的主流。
2、在这样的年代里,诗人要做的是在更纵深的语言隧道里驰骋和建筑自己的房子。(这里说的语言,不是工具式的语言,而是具有精神活性的语言)日益丰富的技巧,导致了诗人多样化的选择,使读者的审美变得复杂和富有韧性。一个碎片化的年代,语言像一地碎花玻璃一样按着某种趋势撒播在古诗和新诗之间的田野上,令人炫目。像魏新河的黄昏飞越十八陵:
白云高处生涯,人间万象一低首。翻身北去,日轮居左,月轮居右。一线横陈,对开天地,双襟无钮。便消磨万古,今朝任我,乱星里,悠然走。
放眼世间无物,小尘寰、地衣微皱。就中唯见,百川如网,乱山如豆。千古难移,一青未了,入吾双袖。正苍茫万丈,秦时落照,下昭陵后。
注:渭水北原上有唐代十八陵。
就是用纯古典的语言意象成功地处理了当代飞行题材的一个典范。
其他,还有用文言或准文言说出今人的思想,比如,嘘堂的很有现代主义技巧的古诗《旦兮》:
布幔寥落兮开一隙,吾与夜兮相溺。
雨倏来而倏止,予荒芜以浅饰。
时有美兮在室,相裸而视兮光仄仄。
汝语吾,何寂寂。吾答,未汝识。
汝之乳兮如蜜,汝之面容莫逆。
吾莫与汝识,如春冬之对译。
乃接枕而默默,犹希腊与哥特。
布幔寥落兮开一隙。旦兮,在即,夜如败革。
还有独孤食肉兽有后现代向俗浅意的城市词《贺新郎·杯渡——东方快车》:
铁屋弥尸气。众男女、梦怀理性,此蒙安启?薄毯难容金字塔,报道有人勃起。辜负了、某声轻喟。楔向时空发源处,亘荒原、蛇眼盈珠泪。谁省得,大乘意。
一车人睡摇篮里。有分教:婴孩时代,慈悲无际。锈托盘中方杯稳,月下悠然飞济。所偕者、钟鸣鸥唳。尔外空明无余物,觉我亦,通透或消弭。驿灯小,泊烟水。
还有直接引用新诗意象和语言的李子诗《浣溪沙》:
摇落寒星大野中,千山顶上起苍龙。一天风色蓦然红。
革命无关菠菜铁,埋人只合亚洲铜。金樽时满亦时空。
亚洲铜,即出自海子诗《亚洲铜》。
还有用白话和文言交互出现,表达出古人境界的诗。比如阿笑的《雪夜访戴》:
那一晚的重点不在黑也不在白。唯独那一晚
拥有无人境的干净
眠觉,开室,四望皎然。一江山川都是天降的神谕
故事里暗示,饮下那杯酒我就是仙,
醉不醉
都不必理会那扇命中注定的门
事实上那晚出走的人再没回来
太和某年,我一次性征用了生命中全部的快
是夜宽袍散发,无君无父,我一个人
葬于一场大雪
还有用古典意象,通过现代技巧,表达出对古典时代童趣式认知的新诗。比如姚月的《团扇》:
月圆藏不见
我不管。只将些旧纸,泥金,瓷青,
与湖色。
画些花鸟江山
(动摇?)
书写绝句是无用的,我指给你看惊鹊,宋代的细骨也嶙峋了
连蒲葵,新裂的绢丝
风物是风物,
小霜是小霜。
还有混杂多种语言,又戏谑又严肃,非古非今的新诗,如拙作《泽国故事》:
泽国千里,谁还会仗剑
去泛舟五湖,击败时间
学学捕鱼术,游泳术,烹茶术吧
一遍遍地重复范蠡的心事
然后提篓入市,内装鲈鱼
忘记吴钩,将驴系于垂杨
笑上酒楼,把桌子一拍
“小二,蒸上湖鲜,来坛好酒”
小二的翘胡抖了一下,高声道
“来了,客官,黄粱已熟,先用餐吧”
还有努力融汇古今语言意象事件,富有戏剧性的杨典的诗《入蜀记》:
噫吁嚱,山是南方的最好
侠隐二字,其本意也就是起伏
另,植物为四川的蓑衣
号古木,最美不过花椒树
我从小就在火锅中游泳
爱一个女人就相当于武装支泸*
记得年,我曾暗渡栈道
经张良庙、武侯祠、剑阁而进入腹地
我看到经济把山水变成了推背图
一只麻雀夜袭川崖悬棺
愁空山下,船夫们满足于吃火
每个人的心态都危乎高哉
挑夫如猿猴,在社会主义的华阳国志中
闪跳腾挪。吊脚楼成为一个特务的美学终点
如今夹竹桃下,再不见蒲扇与袍哥
磨牙吮血,中国人的境界无非
通往三部典籍:吴船录、入蜀记和越绝书
一个右派说他已四万八千岁了
巴山夜雨,早年的朋友们都星散了
我又回到那家从未去过的茶馆
痛饮老鹰茶,并听一个老头鞭策高楼
哦,人无癖不可与交
如林无蛇,夏无雨、江无鲟
如一册孤本无下卷之注疏
我平生最恨之事有二:
一恨白干兑水,二恨峨眉多雾
但我却怀着大遗憾一直活着
还有用口语的语趣描绘了古典和自然意境的湖北青蛙的:
《在兴福寺》
——与风的使者、小雅闲游并坐至兴福寺黄昏
枫香树稳坐在寺院里
有一句没有句地落着叶子
空心潭早已被开元进士看过
秋风在水上写草书
碑文上,如何辨识来去无踪的米芾
移步至池边,对睡意绵绵的白莲指指点点
浮身而出的小乌龟,也有千岁忧吧
得道的高僧睡在竹林,皆已解脱
我身上还有令人厌恶的欲望
我身上,还有盛年不再的伪装
此生毫无意义,偏爱南方庭院,小径
此生偶有奇遇,穿过不同命名的门楣
岁月望远,虞山十里南北两坡各有数百著名坟茔
落木萧萧,使长此以往的天空缓慢看见乌黑的鸟类
两三点雨,落得有什纪念之意?
黄昏把我们放在它味道越来越浓毋须照料的笼子里
还有似乎是在努力复活某种古典语境的飞廉的《立冬书》:
顺治二年,我避兵入剡,
四十年藏书,一日丧尽;
我最好的友人,
则用一口毒酒终结了
六十年的繁华靡丽……
鸡鸣枕上,山中静如太古,
追思往昔,恍如隔世。
最最可笑,人生大梦将醒,
名根一点,犹执意于雕虫。
今日立冬,开门,天飘着
小雪,院中老树,如苏武
匈奴归来,须发尽白。
以上这些都是通过各种古典意象和语言在寻找更多的表达方式。汉语独特性(比如:字形的视觉冲击,文字富含的文化潜意识,音韵节奏的严整铿锵)已越来越突出。
即使在基本与西方同步的现代主义阶段,古典仍是条无法违避的路,如李金发,戴望舒的象征主义(作品从略),至今我们仍为他们的古典语言的余绪和情境感动。而在8、9十年代,古典倾向就变得可有可无,这和古典主义存在的自然基础越来越消失不见有关系,但仍然有些新诗人坚持着,如:张枣的《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对传统意象的现代诠释、南野对自然物像的生态描绘在当时独树一帜;
在当代诗人群中,就出现了很多涉及古典的诗人作品,这或许就是文化认同感的一种表现。除了上面引用的应用语言意像的诗歌外,还有如陈先发的《伤别赋》:
我多么渴望不规则的轮回
早点到来,我那些栖居在鹳鸟体内
蟾蜍体内、鱼的体内、松柏体内的兄弟姐妹
重聚在一起
大家不言不语,都很疲倦
清瘦颊骨上,披挂着不息的雨水
用当代技巧对古典的思想境界重新做出了一番体验和解释;
而汤漾宗的《西施》则走的更远,显然受了下半身的影响,从语言到意境完全西化了,只留有一个西施的空名,但这首诗却获得了真实可信的成功。
“在我的身体里,吴国和越国不过是两条阴茎。”
“这是个好比喻。那么以你的感受,谁更坚挺与泼皮些。”
“面对敌我两种关系,你是否也激荡过类似偷情的欢愉?”
西施没有回答。
古典和当代诗歌如何在后现代语境下达成衔接,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脉,这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要做的大事件。
3、我们如何整合和演进既有的文辞?翻译体横行的阶段,应该休矣。现在本土性很强的口语诗大行其道,也已经把语言的浅层空间消耗殆尽。具有更深层文化潜意识的文言文应该被沿承,被生成出更多的当代要素了。真正能代表中国语言特色的只有文言文,我们却遗弃它很久了,应该是回来的时候了。没有一个国家能真正割断自己的语言史(除非种族灭绝),一个殖民化的阶段已经过去,语言的沙文主义也应该过去了。但文言的演进同时还得伴随着文言语境的演进,所以,重钩文言语境的文化和思想的演进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和思想沙文的主义应该过去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不姓柏拉图,不姓海德格尔,不姓德里达,也不姓马克思,它需要的是,老庄孔孟释禅的复生和演进,在这个基础上,它才可以和柏拉图、海德格尔、德里达、马克思进行公平的交流,而不是非此即彼。我们需要的是复生而不是诈尸,是演进而不是灌输。诗歌因为它语言的实验性和思想的前卫性,会承担这些责任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诗人在当下或将来都会成为开拓者和引领者。
4、或许人们会在50年后(普通话,简体字的出现也不过五十多年),当人们不再为日常用途的便利与否发愁时,文字也许还会出现改革,会越来越倾向于恢复繁体字和创立另一个含有二千年古代音韵传统的官方语言(至少是多元并存),普通话将退化为地方语言,这在近几年的古典文学和书法领域普遍用繁体字的特点可见一斑。(这是个娱乐性的假设)
5、在放开和确立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后,思想和文学就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一个没有思想,或视思想为畏虎的年代就会结束。更加新颖而有深厚理论根据的语言表达形式会不断产生。
6、我想全球的哲学也终会以光怪陆离的碎片形式铺满世界,古今中外形成了一条似断实连的道路。其中中国,阿拉伯,欧美,会因为三大宗教的关系,拥有几片巨大而基本纯净的碎片,它们像北极夏天的冰山一样漂浮着。也许再经过上百年,冰山也会成为一块块普通的浮冰,地球文化将会在交叉融合中变得统一和更加芜杂。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制造一块块从古典到当代的浮冰,并从这块浮冰上跳到另一块浮冰上,直到这些浮冰变成一条宽阔的道路。
7、一个思想影响文学的年代,会带来产生精神境界的升华,而有些感觉的细节就会越来越凸现出它符号式的象征意义,这是一种得意忘形或不拘于现实的表现方式,(这些感觉因为没有具体体验已变成一种纯粹属于文学中的感觉模拟,一种心验)比如闺怨,驴背吟诗等。这些遥远的文化体验所造成的语言意象会不断和科学和城市化的语言意象相互碰撞,最后达到互相影响,杂交,从而形成文化的深厚感和张力!这些在新诗里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但确实没有达到古诗词那种对整体传统精神的深度和精美度的把握。
8、思想带来文学变革的同时,也会带来对真理的冲击,一个充满怀疑的年代会自然产生。由此,还会产生焦虑,虚幻、自由等种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虚幻和自由之间会互相转换,而焦虑则是更具过程性的思想衍生物,它在路上。古诗中对虚幻的追求是一种无奈,因为古人不可能对自由有什么想象,一个觉得人天生应该受管束的民族,只能对规范感兴趣,不可能对自由和芜杂有好感的。虚幻是唯一的安慰。虚幻产生的非抗争,静省的境界,被古人认为是达到圣道的必由之路。二千年来几乎凡以此为准绳的思想都没人怀疑地成为圣学,焦虑成为不受欢迎,思想境界低下的俗学。二千年来的圣学,被庸俗化,成为一种明哲保身,修身养性和为统治者服务的学问。由此,怀疑论者,晚明达观、李贽诸家,晚清诸贤,都成为一种对自身、社会都没有好结果的异端,社会由此进入一种精神滞涨状态!清代中期后的诗歌是这种滞涨的巅峰之作,其古诗词的对既有技巧锤炼的精美度已经和思想的深广度达到了不成正比的阶段。从南朝直到清代的一轮轮诗词精美化的运动,在音韵、语言、意义的纵向横向延伸选择上至此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模仿的好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出路。再做下去,就是一个没有自信力和开拓力的民族所能做的:对精美的匠气的向往,和对可能冲突的异端侵入极力违避,这是对创作自由的极大压制。清代二百多年的奴才体制,已经把人的思维力创造力彻底摧毁,余波至今未息(成龙的中国人天生要管的名言有一定市场就是这种思想的影响)。基于本土思想的开拓,我想只能从晚明诸异端开始衔接。
9、说到创作自由,这里还得说说拉康,他说人的自我是镜像,那么人不妨有许多个自我,(如果自我只能是唯一的,那么这样说就等于没有自我了。)这在文学创作中更能体现。这样就可以解释,唐诗宋词的写作者,可以写出金戈铁马的坎款镗塔之声,也可以写飘然出尘的游仙诗,又能写出莺莺燕燕之音,性别似乎没有阻碍诗人对异性的深入真切的体验。如:李白自信为太白谪世,留下了“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之语;李贺可以为能做上帝的书记而激动;花间词人的艳情诗也是男做女相,姿态万千;葡萄牙诗人佩索亚,生前更是变换过很多身份去写诗,最后把自己的身世搞的像谜一样,或许这些就是多重人格的体现(在网络社会,在文学中,以虚构为真实的作用下,把它们理解成为多个自我更正确)。如果是小说家那更加需要这个功能,心随人事而动,复杂的架构,需要不同或者完全背反的体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设计了(据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的《红楼梦人物谱》统计,共七百二十一人)各种人物几百名,曹氏不可能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原型,只能是模拟和虚构,可见曹氏对人物镜像体验之深。
而同样是对镜像,路遥可以为田晓霞的死而痛哭流涕,虚构,镜像,它不是真实的,却是会让人臆想真实,并为此注入情感。最终的真实似乎永远不能企及,人类或许一直生活在各种虚构组成的网中,我们不断追求真实,却永远只能得到真相。真相,使我们有了更多关于真实的想象,所以我们的创作自由了。创作自由最大的好处就是扩大了我们想象的权利,由此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
10、中国古代的诗人普遍存在一种审美取向,高雅,逸世,本着完善自我人格的体现,和对污浊社会的无奈反抗,这也是无可厚非。一个建立在儒释道基础上的文化,有着对现实的真实违避的企图。对于儒,真实就是对君王的辅佐和对小民的治理,对于释真实就是一切皆是如梦如幻,对于道,真实就是无法也无须改变的自然而然,这些优秀的思想,到后期就成了一种只能不断完善的最高法典,再没有一个宣称是在对真实世界不断怀疑。精神取向的固化,只能由审美细致来体现文学的品质,这几乎成了一种民族的主流性格。比如温柔敦厚,诗教之旨,然而提出这个伦理要求的东周,却是列强纷争,民不聊生;追求这种诗歌品格的沈德潜也没有出什么好诗!而倒是飞扬跋扈的李白,癫狂落魄的徐渭,箫剑轻狂的龚定盦,留下了他们不朽的至今仍值得人们深究的文学遗产。由此可见,诗歌用道德教化众生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更大的功能就是扩大人类想象的权力,和对真实(至少是心理真实)的不断探究。如果诗歌不基于此,迟早会被其他文体超越并淘汰。
————————————
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hl/94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