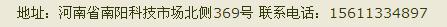柏格曼假面一门分裂的艺术
柏格曼的《假面》,无论是在其生涯四十多部作品或是电影史中都是属于晦涩难懂的,初次观赏时令人痛苦难当,激起的涟漪却又难以抹去。其对于影像符码散的使用、揭发电影本身的后设视角及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造就了它在现代电影中的代表地位。
柏格曼称他透过这部片的制作发现了电影不为人知的的秘密,这样的想法虽不免自我膨胀,但也令人难以驳斥,也许在所有的传播媒介或艺术形式中,只有电影能如《假面》所呈现的那样以反身性作为基调、让形式与内容变得难以区分,让电影变成不只是视与听,更是灼人的、是能被触碰的。
用电影揭露电影
在《理想国》第七卷开头有一段描述大致如下: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像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众所皆知在这段描述中,洞穴墙壁上的影像代表虚无的表象,这是由背后的火光与傀儡所变的戏法,挣脱枷锁的囚徒最终要走向洞外看见阳光下的实体与光线的本质。本片初始,电影放映机的碳棒点燃,发出刺眼的光线。
观众则像是被带往洞穴之外的囚徒,被强迫转身看向火光与在墙上形成虚假投影的胶卷,走向户外,看见雪地中的树林与铁制围篱。电影开头的这一系列画面都指向生命,昆虫、勃起的阴茎、吸血鬼……血腥的影像则像是施加于囚徒躯体上的痛苦。
限制我们活动的枷锁被卸除,掌心却被钉于木条之上,负上更形沉重的十字架,囚徒所获得的自由并不是毫无代价的,而是透过献祭所交换的,思索何谓电影与思索何谓本质是同样痛苦的,看见事物本身并不意谓思考的停止,更多的疑惑必将接踵而来。
据医生所说,伊莉莎白在一场演出之间突然就不说话了,隔天她并没有出现排演,她被家中仆人发现躺在床上,至今不语的情形持续了有三个多月。伊莉莎白不回应丈夫的来信、将儿子的照片撕成两半,将自己从一切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
护士艾玛是一个与伊莉莎白全然对比的角色,她热爱他的工作,甚至她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护士;她计划将与卡尔亨利克结婚、将会生下好几个小孩,一切都是决定好的,都是内在于我的,她对着镜头如此介绍自己。艾玛似乎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至少看来她是这么想的,也因此她难以理解伊莉莎白的病情。
在医生建议伊莉莎白可以到她的度假小屋去静养的那一场戏中,医生向她说:
……无望的恶梦,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本质上的,每个梦醒时分都在时刻警惕。两者之间的战争,别人怎么看你和你究竟是谁,一种晕眩的感觉,一种想最终被暴露的持久的渴望,希望被看透、被击倒,甚至被淹没。每个欺骗的谚语,每个虚假的表情,每次苦涩的微笑。
自杀?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可以沉默和静坐,至少你这样就不用撒谎了。你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把世界关在门外,这样你无需扮演任何角色,做任何虚伪的手势和表情,你是这么想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你的藏身之所也并非是密不透风的,到处都充斥着生活的骗局。
你不得不做出反应,没人在乎你是说实话还是撒谎,那是只在剧院里才变得重要的事,或者甚至在那里也不是重要的。我懂你为何沉默,为何不动弹,你的毫无生气已成定局,我能理解,而且很钦佩,我想你应该要在这件事平息之后再扮演这个角色,直到人们不感兴趣,你便可摆脱了,就像你摆脱其他角色一样。
这段独白无非是柏格曼欲透过本片进行的批判(可能是针对自己,也可能是针对电影本身)的引言。一个足够诚实的演员必然曾经深究过在演出当下的微笑究竟是出于与角色本身的融合,或是表演毕竟是作为一种职业,因此必须在某一刻给出正确的,或至少符合剧本与观众期待的微笑。
并没有任何一个位置是如此称职地作为一个纯粹被观看的角色,在演员身上能够见到被放大了的表象与本质之间、诚实与谎言之间的矛盾。
医生质疑伊莉莎白的病情,因为若自杀是对生命的反对,那么不语以及不行动就是对表演的反对,那么呈现电影的肉身就是对电影因试图再现而无法摆脱的欺瞒性的反对。
伊莉莎白若是陷入震惊的状态或是精神的崩解,至少可能会做出对生命的伤害,而不是沉浸其中,然而她不会也不可能自杀,从她在病房看见释广德自焚的影像可以得知,她无法理解对于表象的全然毁灭。
她选择拒绝言谈与行动,拒绝回应世界的刺激,就像是导演有意揭露影像的原理,而非躲在镜头背后默认光影与布景制造出来的假象并企图消弭摄影机的存在,而非躲在一种可能会是柏格曼所认为的虚伪态度中。
凝视镜中/步入镜中
两人到了海边的小屋,伊莉莎白的病情渐渐有所好转。艾玛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直到这样的照护关系主客易位。艾玛持续和她说话,分享自己在所有事情上的感受,最后却变成了某种心理治疗。
在艾玛完全坦诚(她告解了自己在海滩的那段经历)后的那个梦境般的晚上,两人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景点(镜头特写于两人的面部),伊莉莎白如幽灵游荡,进入艾玛的房间,轻轻掀起她的浏海,两张美丽的脸庞出现在我们面前。均质的光投照于两人,她们直望观众,却像是看着镜中的自己。
转折点发生在数日的午后,艾玛在伊莉莎白寄出的一封信中发现伊莉莎白在利用自己的坦诚,甚至将自己当成了某种有趣的研究对象。而后艾玛出于想要测试(或是报复)伊莉莎白,佯作不经意地将玻璃碎片散落一地让她踩上,艾玛则在旁静待这一切的发生。
在两人视线交会的这一刻,艾玛的脸庞瞬间出现一道刮痕,放映机发出刺耳的喀喀声,画面从正中心开始溶解。
这或许可看作是意义的销毁、(出于愤怒而导致的)印象的崩解,但也可看作是内容与形式融合的起点。在这一刻不仅呈现电影的躯体,更呈现胶片与肌肤共有的单薄的脆弱性,其打断了电影独有的时间性,更跳脱了蒙太奇理论的限制,让剧情的时空与现实的时空被并置,重新提醒我们本片真正要
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zz/152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