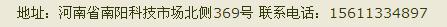本土文学小说集大姐连载17王晨
1
那年大姐刚满20岁,父亲说:“丫头大了,留不住了,戴上大红花嫁了吧。”大姐便嫁了。待添箱客那天院子里摆了好多桌子,父亲杀了一口猪两只羊,说把事情要过得光彩体面些。大伙一高兴,有几个家伙就操起了两把二胡和一面小鼓又拉又捶起来。
开始拉的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后来提壶传酒的人往那几位跟前跑得勤,那几个头一喝大,胆子一正,拉上了“干妹子走路水上漂,不要闪了哥哥的腰……”人群中就有人扯开嗓子吼上了,把小曲子、眉户放开了唱。
后来越唱越邪乎,有一个喝得舞马长枪,便拉着哭腔唱起了《小寡妇上坟》,还鼻子一把泪一把的,他唱道:“前圈里的骡子,后圈里的马,可我的哥哥呀你在哪达?奠几张烧纸青烟冒,倒一碗黄酒土吃了……”
他一边唱,一边还道白:“哥哥呀,你咋不等我啊!”他被主事人骂了一顿后,好像才从前天埋葬了村头老赵头的丧事中醒悟过来,知道我家是在办喜事,便跪在父亲面前一个劲赔不是,还煽了自己两个耳光。等一转身,他那嗓门更高:“手提瓦罐身穿孝,三寸大金莲白鞋包…”唱的还是那个调子。
后来鼓点就有些快了,拉二胡的两个人完全不着调,互相跟不上趟,闭上眼睛在那里左摇右晃,那声音比半夜里要出去撒尿的狗崽子挖门的声音还难听。
我跑过去趁那鼓手端起杯子又喝酒时,拿起鼓槌一顿乱敲,还在摇头晃脑拉二胡的贾禄林的头上敲了一下。贾禄林喝得像个红头鞑子,操着浓重的甘肃民勤腔结结巴巴指着我对父亲喊道:“这个鸡巴,把、把、把点子全敲乱了。”
那天事情办得很红火,大家喝得都开心,不开心的就是许二球。“许二球”是他的绰号,真名叫许成魁,他说话带些二球劲,所以大家就那样叫他。那家伙是个光棍,好给人帮忙,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但还很要面子。人家都说他是:蚂蚁衔了个榆钱子,耍了个要命牌牌子。
许二球来得很早,主动承担了挑水烧水的活儿,干得很卖劲。他肯定是肚子饿了,要不他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也是父亲请的主事人的疏忽,竟把许二球忘在了脑后。当主事者向大家喊到:“今天大伙既是东客也是稀客,自己的客自己待,没上桌的上桌,没坐席的坐席。”
于是大家互相让着上桌就席,可偏偏就忘了许二球。当许二球看到第一拨人下了桌子,第二拨人上桌时又没让他时,他瞅瞅主事者,一下发了火,他跳到院子当中,手里提着半截烧焦的还在冒烟的柴火棍喊道:“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把我许成魁当成啥了,我在这里忙活了半天就没人看见吗?这也是客那也是客,难道我就不是客吗?在你们的眼里,我光有干活的命,没有吃饭的嘴,我到底算哪门子客,既不是东客,也不是稀客,难道我是嫖客吗?”
当下许二球就被主事者让上了桌,说了几句好话,拿几杯烧酒一灌,许二球就咧开嘴笑了。这时,唱《小寡妇上坟》的那位一步三晃地走到许二球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嫖客,我是嫖客,我是嫖客该行了吧?”许二球这时也喝晕了头,对着那家伙说:“你、你当然是嫖客。”主事者便对许二球说:“以后说话文明点,你老是球鸡巴头子出气,带着一股子尿腥味。”许二球喷着满嘴酒气说:“没麻达,只要有酒喝,保证没骚气。”
第二天,陈业青,就是我后来的大姐夫和几个人吆了辆双套马车来娶大姐,马头上虽然戴着红缨子,那车把式鞭花甩得也很响,但还是被挡在了大门外。原因是那辆马车惹得舅舅不高兴,说拉边套的咋是一头骡子,太欺负人了。当时我不太懂,后来才知道骡子不论公母,配不了种也下不下驹。陈业青当时就楞在了那里,一看就知道他也是球事不懂假装老总的下家。他直戳戳地立在大门外候着,和他相来的人吆车返回又跑了十多里,把骡子换成了马,大姐才像父亲说的那样带着大红花被陈业青娶走了。
2
陈业青进门时,一挂鞭炮就把他的屁股炸懵了,进门后瞅着那多的凳子不知往哪儿坐。当他被允许和陪女婿一起被让上正屋的桌子后,他显得更加尴尬和不知所措。调皮的二姐从他手中抽走筷子,换上了一尺多长的两根芨芨棍,又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塞进他的怀中。陈业青知道要他吃出饺子中的硬币,但两根芨芨棍在他手上却不听使唤,一着急把一根还窝折了。他第一口就吃了个“狗球尖尖”辣子面包的辣饺子,辣得他像猴子吃了蒜一样直甩头。第二个又吃了盐面包的咸饺子,二姐问他咋样,他说苦。后来又是花椒面饺子、胡椒粉饺子。等他吃出包有硬币的饺子时,除了满头大汗,嘴里被辣得拿出手帕直擦舌头,直到娶大姐走时,他嘴里还在丝丝地吸着凉气。
大家当众看着陈业青出丑,真正开心了一回。父亲也开心,但他觉得有点过头,对着二姐翻了翻眼睛,咳嗽了两声。他觉得不能太过分,不管咋说,那以后就是自己的女婿啊!二姐才不管那一套,她竟跑过去对着父亲的耳朵叽叽咕咕说了句话,只见父亲偏过头对着二姐瞪了一眼,转过身出了大门。后来我问二姐她给父亲说了啥?二姐说:“红豆腐呀!”我一下笑了,二姐算把住了父亲的脉门。
二姐说的是父亲过去当队长时第一次到县上开三级干部会议吃红豆腐的尴尬事,这事只有父亲个人心里明白。那是在吃早餐时,父亲见服务员端来的一个小碟,里面只有三小块东西,他从来没见过,旁边一个人说:“这是红豆腐。”父亲心想,这指甲盖大的三小块东西够谁吃的,碟子刚放下,他筷子便伸了出去,一块红豆腐被他的筷子牢牢夹住,他一张口就吃了。当时父亲的表情难以形容,他嚼了红豆腐一下便停住了,他紧闭了嘴,用舌头顶着红豆腐不知咋办。父亲是个粗喉咙大嗓子的人,吃饭时总是狼吞虎咽,看看桌上其他人,大家都用眼睛看他,他便硬着头皮把红豆腐挤在天花板上用舌头压扁,脖子一伸把红豆腐囫囵咽了下去,那红豆腐带有的酒香味,他根本就没体验到。这事儿他谁都没告诉,还是一次喝多了酒当着全家人的面自己说出来的。我问他当时嘴里是啥味道,他和大姐夫吃饺子时的回答不一样:“灰他祖宗,咸。”从那时起,父亲既是第一次吃红豆腐,也是最后一次吃红豆腐。后几次到县上开三干会,看到人家在热蒸馍上抹上红豆腐吃得津津有味,他自个就不好意思了,在心里自己就笑了。
3
在席面上忍气吞声任人摆布的大姐夫陈业青,确实有些窝囊,后来的事便印证了我这个看法是对的。而大姐的脾气却跟了父亲,占住理儿不饶人,能把狗说得夹起尾巴钻在狗窝里不再出来,用两只大眼扑瞪扑瞪望她;能把猪骂得把食倒进槽里都不敢往前试看,转着磨磨直哼哼。
陈业青虽然娶走了大姐,但大姐一直不让他上手。三天上回门,父亲一高兴,把家里一只三岁的母鸡宰了。俗话说,鸡儿下铁蛋,麦子打八担,但我家的麦子却没有打上八担。父亲说那鸡简直就是一只骚老鸹。那只母鸡长得很漂亮,有公鸡的风范,它长着一个咕咕头,冠子是黑紫色的,要要俏、一身孝,它身上的毛一色白,尾巴像公鸡的尾巴往上翘,走起路来挺胸仰头,爪子抬得很高,一下一下,像当兵的走正步。但一辈子就下了一只孤蛋,蛋太大,把屁眼都绷烂了,从此落下了毛病,看见别的鸡下的蛋就用嘴啄,嘴里咯咯咯地叫,像要报仇一样。父亲见它光吃不下蛋,骂它是铁母鸡,想把它收拾了,但母亲不让,借着大姐她们回门的茬,父亲才遂了愿。我到后来还时常想起那只母鸡,并且对它有了新的认识,它比我们那里的人都要超前,它是那一方家禽里面执行计划生育最好的范儿,结果被固执的父亲杀了。
饭菜虽然丰盛,但全家人从脸面上看得出来,大姐不高兴,大姐夫脸上也没表情,唯唯诺诺的,有腿不会挪,有手没处搁,有嘴就更不会说了。除了全家人吃饭待在一起,其他时间大姐和二姐都是在原先她们住的屋子里叽叽咕咕。大姐根本不去理会大姐夫,就像从未见过和从不认识一样。母亲看出了点门道,吃完饭便打发他两个回家,说嫁出去的丫头回门时屁股不能太沉。我和父亲则傻里呱几啥也没瞅出来,我还是缠着让大姐多待一会儿,让她说说结婚好还是不好。后来大姐夫瞅瞅大姐,大姐沉吟了一下,咬了咬嘴唇说走吧,大姐夫便跟着大姐走了。出了大门,没等大姐夫动手,大姐顺手牵过门边驴槽上上拴的驴,脚踩驴镫,自己就骑上了驴背,一甩鞭子驴就颠起了碎步,大姐夫则一溜小跑,像个跟班的,脚底下倒很利索。但我心里想,大姐夫陈业青太熊了。
4
过了个把月,大姐夫一个人垂头丧气地来了,他显得前怕狼后怕虎。看得出来,他是硬着头皮在西屋里给父亲说了几句话,出来后父亲和他的脸色都很难看,他没抬头看其他人,快步走出了大门,母亲喊他,他也没回头。晚上我听到父亲向母亲嚷道:“还算个儿子娃娃吗,丫头嫁给了他,日不上那是他的事情,在我当老子的面前说这话,他也真能说出口,那么个本事还娶婆姨,还不如拔上一根球毛,上吊吊死算了。”母亲则“嘘嘘”地让父亲小声点,而且用手直指我和二姐的屋子。第二天,我看到下地的父亲没有干活,铁锨扔在一旁,坐地埂上死命地抽烟。
那一段时间,父亲的烟抽得很厉害,我劝父亲少抽点,他一下翻了脸,对我吼道:“鲜肉坏的快,还是熏肉坏的快,再胡说我煽你的耳根,给你一个屄斗。”
后来大姐夫和大姐一块又回来过几次,但都闹得不甚愉快。母亲悄悄把大姐叫到伙房里,一再给她交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还搭在她的耳朵上,说些体己话,一脸的责怪。但大姐根本就听不进去,她每次回来都要在伙房里烧了水,在她原来住的房子里洗澡,洗好长时间,出来后长长地舒一口气。
俗话说,岳母见了女婿,就像坐窝的母鸡。为了打圆场,母亲说了好多话,他对大姐夫献了很多殷勤,老是劝他多吃一点,还夹菜往他的碗里送。她每次都想法把饭做得好一些,多弄几个菜,但父亲却不高兴了:“吃那么好干啥,吃完了到哪儿拉屎去?”看得出,他对大姐和大姐夫都有点不满。
再后来村上的人便传开了,说大姐和陈业青不和,他们胡诌说,陈业青开头是忍,中间也是忍,两人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能坐到鸡叫。到后来大姐夫实在忍不住了便和大姐大打出手,每到晚上夜深人静,家中会突然爆出大姐的哭闹声和大姐夫的叹气声,中间夹着摔窗子打门的声音,那些声音惹得全村的狗整晚上在大姐夫的门上狂叫。
这天,村上一堆男人在一起喧话,他们根本就没留意到我,也可能是故意说给我听,让我当个传声筒,把这些话传给父母或大姐。一听他们就是胳膊肘子朝外拐,他们说大姐从嫁过去晚上就没脱过衣裳,系着三条裤带,绑得全是死结,陈业青怎么折腾,也是百撕不得其解。有一晚上说陈业青费九牛二虎的力气把裤带解开,但天却亮了,终究没弄成事情。他们说不相信收拾不住一个女人,搁上我捶死她。他们还说陈业青应该用些老旧的管用的办法,找两个亲戚压住大姐,强行施暴,只要睡上一次以后就顺当了。他们说陈业青是个好小伙子,是个过日子的人。说我大姐一看就是汤里头的葱花,药里头的甘草,人面上能站住的角儿。车轱辘没油不转,女人没球不站,这女人站不住的原因是不是已经有相好的了,要不然不会是那个样子。
5
事情还真让村上的人说准了,大姐结婚前就是有个相好的,那男的叫刘春明。刘春明是大队机耕队的拖拉机手,春天和秋季是他最忙的时候,春天春耕耕到星星上来,秋天秋翻翻到太阳下去。大姐和他是在大姐去大队学校给我开家长会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大姐走在路上,大队离我们村有10里路,那天太阳很大,把路边的草都晒焉了。大姐走了一身汗,这时后面来了一辆拖拉机,大姐回头一招手,拖拉机就停了。开拖拉机的是刘春明,搭那时起,大姐就和刘春明开始来往了。
大姐和刘春明好了一段时间后,家里人才看出来点苗头,后来母亲问起,大姐才说了实话。但父亲一百个不同意,原因是大姐和陈业青是自小定下的娃娃亲,加上大姐夫的老家也是山西的,乡党的因素占了上风,父亲说啥都要成了这门亲事。他就开始给母亲说常说那句话:“丫头大了,留不住了,戴上大红花嫁了吧!”父亲的这番话,加深了大姐的反感与叛逆。大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嫁,就是嫁了也要离婚!”
父亲则不然,他知道只要大姐嫁过去,过些日子就会烟消云散,现在说的都是气话。谁知大姐嫁给大姐夫后,就把事情搞得一塌拉糊涂。
刘春明和大姐夫陈业青比起来,刘春明要英俊的多,精明的多。在机耕队当拖拉机手的都是吃八方的人,都说机耕队要解散,但还在集体作业,谁知道到哪辈子才实施。他们是地耕到哪儿,就吃住到那儿,各生产队为了深耕地块,侍弄好土地,赶季节、赶时间,对机耕队的人都敬三分,机子一进村,就把羊宰了,临时的小灶把机耕队的人吃得优越感十足。刘春明见的世面要比大姐夫广,嘴也比大姐夫会说,自然,大姐夫和刘春明就无法相提并论了。
6
大姐和大姐夫离婚时,大姐夫坚决不离,硬是拖了两三个月,这三个月中,大姐对大姐夫是冷水浇心,到了冰点。无论大姐夫怎样找话茬,怎样赔笑脸,大姐脸上冷得还是让大姐夫心里发抖。每天看着大姐阴沉的脸,听着大姐一句半句戳心窝子的话,大姐夫只好放弃了坚守,说穿了,也是在大姐的再三逼迫下,大姐夫无可奈何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在离婚之前,大姐夫心里有多苦,不得而知,离了婚是怎样的心灰意冷也是后来才略知一二的。但发生在大姐夫身上的一件事说明了他的心理活动也是很复杂的。听他们村上人说,大姐夫有一次骑着驴把驴丢了。当他骑驴去大队的醋酱房买了醋后,出了门自己就背着醋笼子步行回去了,等下午给驴槽里添草不见驴时,想了半天才想起把驴丢在哪儿了。他返回去找驴,但还是没找到,原来那驴悠悠荡荡自己回来了,到了家门口,驴没瞅见大姐夫,踌躇了一会儿,便一回头找别人家的草驴干仗去了,等大姐夫找到驴,那驴打着响鼻正在场边的干粪堆上高兴地打滚呢。
大姐就更不用说了,离婚前的一段时间我从大姐身上看到了她的心绪不宁和不悦。她先前是若有所思,到后头就有点发呆和恍惚,有时你和她说话,你问山里的椽子,她回答是树上的猴子。你说吃饭了,她说没电了。你说该睡觉了,她说你吃胖了。问非所答,简直就和聋子一样。
让我记得最清楚,最不能忘掉的是大姐摔锅那一次,后来我分析,大姐的脑子绝对没有进水,肯定是短路。在那一刻她想得一定是刘春明,不然那次她不会洗完锅后把锅端出去倒洗锅水时连锅带水全都扔到了雪堆上,那锅和水都是热的,雪水迅速融化,那锅就沉进雪堆里去了。晚上母亲做饭时便找不到锅了。父亲说:“就是把人丢了锅也不会丢啊,把吃饭的的家伙丢了,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咋没把嘴和屁股也丢了,不吃也不要拉了。”但母亲就是找不到锅,连猪圈里都找了,怕是谁连汤带水把锅端去喂猪了,但还是没有。父亲又说:“可惜了那个苏联货,带四个耳朵,敲起来脆生生的。多少年了,比二姐的岁数都大,让油煨透了,黑亮黑亮的,多好的锅啊!”
全家人百思不得其解,时逢腊月二十三,不成连灶王爷一起上天了?这成了父母亲的一块心病,直到春天,雪消了那锅重见天日后,父母的心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怎么都想不通,那锅是怎么到了雪堆下面的。那时大姐已远嫁到了长山窝子,这锅怎么到了雪堆里,成了我家的一个谜。直到后来大姐来家看父母时,谜底才被解开。大姐说:他是在一个晚上想全家人的时侯,突然想起来她把锅扔进雪堆里了,她在被窝里笑成了一团,后姐夫匡富来被她吓了一跳,问她咋了,她还是一个劲笑,后姐夫再问她,她又捶着匡富来的胸脯笑,后姐夫以为她神经错乱,医院,她却抱着后姐夫抽搐着笑。她想写信告诉父母,一想,还是当面说了才好。大姐从长山窝子回来看望父母时,在灶上又仔细地看了那锅,对着锅又笑了起来。父亲说:“灰他祖宗,锅一丢,人的魂也丢了三分,去供销社又买了一口锅,供销社的老马问我买锅干啥用,我说喂猪。”
父亲说的全是实话,他怕路上又有人问他买得啥,他用麻袋把锅装上背了回来。新锅买回来后,父亲用砂纸把里外的铁锈打掉,先用它煮了几次猪食,然后再给人做饭,但做出来的饭还是有一股铁锈味,全家人吃饭时鼻子都一吸一吸、眉头一皱一皱的。
7
大姐与陈业青准备结婚时,刘春明就像是丢了魂,就在陈业青娶亲的前两天,他还一次次要找大姐说话。大姐给刘春明讲,父母逼得太紧,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怪就怪清末民初那会儿,先人们走西口,一块从山西老家大槐树出来,拉骆驼做买卖,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因为骆驼被土匪抢了,买卖赔大了,折了本,做起了小本生意,好在把命保住了。年那阵子,城镇人员精简下放,才分别在农村落了地,但还是到了一个乡上。到了父母这一代,走动就没停过,所以才订了娃娃亲,既然定了亲,父母坚持要兑现,说不能哄了人家,她确实也是无可奈何。
大姐与陈业青完婚,刘春明倍感失落,不想和人过多交流,多余说话。和他要好的几个问他和大姐的事,他说:“随行就市,就那样吧!”回答的不伦不类。
人们常说家有千贯,出气的不算,刘春明家里养有十多只大尾绵羊,膘情好,脊背都吃平了,像案板一样,走起路来尾巴就像穿着高跟鞋女人的屁股左右扭动。有人便给他父亲说,这两天蛤蟆大的羊都能卖个好价,你们的羊也该出手了。刘春明父亲的两条罗圈腿像两个筐把,甩着腿推开刘春明的门,安顿刘春明去把羊卖了,但刘春明为大姐和陈业青的事闹心,躺在炕上装死狗。
仅仅过了三天,他家的羊便在圈里横冲直撞,开始死了,而且来势汹汹,没有几天,就死得差不多了,躺在炕上的刘春明也急了。这羊到底得了啥病,没人知道。县防疫站来人一检查,把死了的羊都深埋了,把剩下的几只也拉回去处理了。一个老鼠害一锅汤,整个套子湾乡的羊都不让外卖了,连通乡镇的路口上都设了卡子,这把刘春明搞得心里像球戳了一样难受,头甩得像裆里的锤子。等事情过去他才知道,防疫站的人当时回去就向县上汇报了,是口蹄疫。好在疫情不大,属突发性,全乡统共也就死了七八百只羊,风波很快就过去了。
刘春明自认倒霉,对象被陈业青娶走了,羊也死光了,真是祸不单行。从那一刻开始,他对大姐就有了一股子怨气。大姐和陈业青离婚后返回头找他,他便把怨气出在了大姐的身上,他面对大姐闹腾不是闹腾,脾气不是脾气,反正是哼哼哈哈的。
大姐说:“我是清白的,为你守住了身子!”刘春明说:“谁能证明你的清白?”大姐指着刘春明的鼻子说:“刘春明,你不是人,你等着!”大姐立马从怀里拿出一把菜刀,右手举起刀,伸出左手食指,挥刀就砍了下去。刘春明一把抱住大姐,连声说道:“我娶、我娶、我娶还不行吗!”
刘春明万万没想到,大姐说到做到,一点含糊都没有,性子那么烈、那么直,万一出个事情,他可怎么担当。而大姐事先也想好了,如果刘春明不要她,她也只能用死来证明自己。
文章来源:最后一公里奇台县气象局
本期编辑:海涛罗小依
本期审核:陈艳萍
投稿邮箱:
qq.北京那家白癜风医院最好北京较好的白癜风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zz/87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