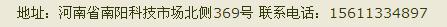小说连载越境四
编者按:士兵麻羊羊,哨长张和平,一个死于笔,一个死于枪。一个“越境”于人性,一个“越境”于法纪,30年的轮回自戕,历史的残片与眼前的屏闪,时间的切割不过抽刀断水水更流----长篇小说《越境》,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勇气和真诚,旷世展现了一段家国情仇的迷幻故事,泣血讲述了一个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件。军人总是被政治伤害。军人必须忍受政治的伤害。《越境》的实践意义,不只勾陈翻晒历史与现实转捩捭阖的怪诞奇诡,更在于展示军人生命个体的悲情和人性光芒的坚忍泼洒与豪迈绽放。同时,也使得时下较为稀缺的文学良知,在一个未知的小说疆域中的妥帖安放,成为可能。小说构思新颖,结构独特,文笔洗练简洁,语言优美生动。
第七章
提要:琪琪还是头回听到有人叫她小狐狸精,就去照镜子,仔细研究自己的面相,试图在上面抓到“小狐狸精”那四个字,结果不够理想。她知道高莲秀不是省油灯,眼光毒着呐,她说自己是小狐狸精,一定是有真凭实据的。她决定帮着高莲秀找找“真凭实据”,脸上找不到,就别处找找看。夜里,进了洗澡间,脱光衣服,让自己披头散发白白嫩嫩地立在镜子前。
琪琪一见到躺在病床上的爹就哭了。“爹呀,你咋整的呀,怎么躺在这儿了?”琪琪的双手像两只蝶在龙建华身上翻飞忙碌着,摸摸他的腿,捏捏他的胳膊。
医院的。
龙江可不像琪琪那么没出息,进了病房,眼睛朝病床上扫了一眼,便开始打量一下四周,选个地方,把琪琪和自己的行李放置好。早在双脚踏入病房之前,他就寻问了护士,弄明白了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没屌事。也就屌大的事。这时见琪琪方寸大乱的样子,凑上来,没心没肺地说:“你多哭两声,把我那份带出来!”
琪琪推他一把,冲龙建华说:“爹,看你这破儿子……”
龙建华抓着琪琪的手,眼睛望着龙江问:“王九成给你的假?”
“是──我请了假。”
“人家张铁石替他请的假。”琪琪斜了他一眼说。
“我没什么事了。”龙建华对龙江说,“省军区派出的调查组今天就到你们团。连队情况怎么样?”
“正常。”
“连队出了那么大的事能正常吗?”龙建华显然不满意龙江的回答。“在家待两天,赶紧给我滚犊子!”
“是。犊子准备第三天就滚。”
“爹,”琪琪对龙建华说,“我哥回趟家不容易,他连里那个指导员挺强的──再说,你好不容易病一回,我哥希望多在你眼前晃悠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
“哎呀,”龙建华嘲弄地说,“真不愧是当翻译的,嘴真会说!”
“那是。”琪琪朝龙江使眼色。“龙连长你信不信,咱爹肚子想说没说的话我也能翻译──”琪琪学着龙建华的口气,“龙江你个小犊子,别光在这儿卖呆儿,去给老子整点儿吃的去!”
龙建华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嘿,听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儿饿了。”望着龙江说,“打电话让你妈包二十个茴香馅饺子……包七十个──你们俩也没吃饭吧?”
“干嘛总这么精确,累不累呀,真是的!”琪琪嘀咕着,把被子给龙建华盖好。
“爸,”龙江见有机可乘,码着琪琪的话顺上一句,“你这病……你自己是不是已经精确地做过身心损伤评估?”
“反正没什么大事。”龙建华说,“医生也这么说。”
“哥,饺子……”琪琪提醒龙江。
龙江摸起床头柜上的电话。
龙建华有点儿犯难,乌兰回来过的事,要不要告诉琪琪?母亲回来了,这样的消息对琪琪全面封锁,似乎说不过去。可是,龙建华不敢贸然行事,因为那样做极有可能牵扯出一长串的故事。故事太长,也太过复杂,复杂到用讲述这种方式根本无法拆解的程度。况且,时机尚未成熟。乌兰显然明白这一点,她并没有跟自己提琪琪,而且一直只字不提。这二十年间,她竟然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来过电话,也没捎过口信,不管女儿,不探问母亲──她把她们囫囵个儿打包交给了龙建华,一心一意守护着小白。她知道只能剃头挑子热一头,自己只能顾一头,而她只能选择小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乌兰的做法,有点儿像大兴安岭深山老林里误入圈套的狼。打狼的都知道,狼踩中铗子,如果猎人不及时赶到,它就会一口咬断自己被夹住的腿逃之夭夭。搁在人类这里,这种行为叫“壮士断腕”。
这次,乌兰的突然出现,中心内容是处理小白的事,这个判断应该是准确的。但有一点,那个被岁月尘封已久的故事,也将被重新掀开──乌兰这次回来,分明就是启动故事的枢纽。那么,现在看,琪琪暂时要站在故事外面,她入局还为时尚早。还有一个难点,乌兰的出现,到底可以瞒过琪琪多久?咳,走一步看一步吧,等她知道了再说。只能这样了。不这样又能怎样?有时,龙建华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两难的漩涡里挣扎,最终总算能脱困上岸,可是事后,这种脱困本身反倒会更加困扰他,让他陷入更大的矛盾漩涡。即使是处理家庭关系也大抵如此,比如,他把琪琪和玛丽娅索放置在身边,却不得不轻慢了高莲秀。
还有龙江和琪琪。为了琪琪,他只有把唯一的儿子从自己身边推开,可这又在父子之间、兄妹之间埋下不可知的麻烦,也许是个更大的麻烦。
高干病房很清静,外面的走廊里,除了护士走过时鞋底磨擦地面的嚓嚓软响,几乎很难再听到别的声音,所以,高莲秀和姜英超从电梯出来,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动静。主要是听到了姜英超声音。她这个人巨大的特点就是制造声音。
“──往这边高姨!待会儿我检查一下,看他们都给龙叔叔用了什么药。”姜英超说话的语速很快,那些话是翻着一串跟头从她口中蹿出来的,顶得的门哗地开了──琪琪从里边挡了一把虚掩的房门。琪琪望着龙江说:“我嫂子来了!”见龙江不动弹,就拿眼睛催促他。龙江有些不情愿地走过来,跟随在琪琪身后出了病房。琪琪朝高莲秀叫了声“娘”──这是从龙建华那儿顺下来的叫法──接过高莲秀手中的餐盒,刚要叫声“大超姐”,身上就挨了她一家伙。“从边防回来也不报告一声!”琪琪身上吃了疼,怕她再来一下,忙闪开,嘴里说:“你进屋收拾我哥去,他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姜英超说:“是不能放过这小子!”琪琪说了一句俄语,然后凑近姜英超,对着她的耳朵压低声音,“相信你的实力──最好能让他爬着回边防──爬不动。”姜英超作势朝琪琪身上掐过去,吓得琪琪忙躲到高莲秀身后,冲着站在门口的龙江说:“我嫂子欺负我!”
“这儿是高干病房!”高莲秀提醒她们。其实两个人一直是收着的,动作和声音至少都缩了一圈。听了高莲秀的话,她们立即再收缩了自己,人规矩下来,分别站在高莲秀两侧,拥着她走近的房门。
“妈!”龙江迎过来。
高莲秀上上下下打量着龙江。“晚上没睡好吧?脸也没洗。”
龙江侧身,让高莲秀先一步进门。他扫了姜英超一眼,随口说:“怎么也不换套便装?”
“忘了。”姜英超说。
“下午让琪琪带你上街去整一套!”龙江说。
“行,我再买双运动鞋。”
琪琪忍不住,嗤地笑出了声。这就是姜英超,从来不吃亏。
姜英超那儿还不算完,冲龙江弹出两根手指:“AA──你硬让我买的,鞋钱你出一半!”
姜英超很少着便服,衣服也没有换来换去的习惯,一年到头身上裹着一套军服,用她自己的话说,省事,不用化妆。省心,去哪儿都没人敢惹。龙江笑她,谁惹你呀?谁敢惹你呀?琪琪说她是个进攻型选手,即便是跟人聊天,也跟打仗似的。了解她的人都知道,此时第一要务是必须站稳立场,最好有个根据地,也就是找个位置先坐下来──你可不能站着跟她聊,否则,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她就把你逼到了边角地带,让你转下身都困难重重,只能直着眼,看她的嘴机关枪一样朝你突突。见到姜英超,琪琪的脑子里偶尔会蹦出一个让自己脸热心跳的问题:和龙江做爱的时候,姜英超会把龙江折腾成一副什么熊奶奶样呢?一个挺有趣的问题,缠绵又热辣。这是一个可以有上千个答案同时又没有答案的问题,琪琪无法搞到答案,只好独自咯咯一乐,跑到镜子前照下自己胀红的脸蛋,了事。
很自然的,她也想过自己和龙江,并让自己偷偷地把姜英超置换出来,可是一切都不对劲,哥还是哥,妹还是妹。她可以妹妹找哥泪花流,一找找到天尽头,却不可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热泪流,完全不对劲,所以龙江积存多年的想法根本无法在他们的关系中得到具体落实。琪琪不是傻瓜,龙江爱上她的日子可不短了,至少应该在十年之前,因为就在那年的八月份,龙江跟龙建华大闹了一场。龙江和龙建华的父子战争采取是冷战的方式,他们俩谁都不跟谁说话,谁都不搭理谁,静悄悄的,可结果却是个大动静──龙江不再继续读高中,等着年底征兵走人。那年,龙江十六岁,琪琪十四岁。当时,琪琪并不知情,只是影影绰绰地有些感觉,那爷俩掰成那样,是跟她的突然转学有某种关联。琪琪转学的决定非常突然地下达了,连她自己也云里雾里。在这件事情上,高莲秀反常地跟龙建华站在了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瞄准龙江扣动扳机,单发、短点射、长点射,杀得龙江血流成河,身上都是筛子眼,毫无还手之力。唯有一点不同,高莲秀于“射击”间隙当着琪琪面念白,“你这孩子呀,到了外边可要学会懂事,除了好好学习,还是好好学习,更好地好好学习,记住了没?”听上去有种亲切的无奈。她在自己的丈夫跟前却不是这么念的──“咱儿子是迷上那个小狐狸精了,她可害惨了我儿子。”这话让琪琪无意中听到了。那天,她本来还可以再听到一些,可是,她突然发现了龙江。龙江显然也听到了这样的话,而且不止,远远不止这些话。他应该在她之前就在听,听到了什么更重要的话,不然,他不会用那样的目光看着琪琪。当时,龙江突然看到了琪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像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然后,低下头,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琪琪还是头回听到有人叫她小狐狸精,听了高莲秀的话,她就去照镜子,仔细研究自己的面相,试图在上面抓到“小狐狸精”那四个字,结果不够理想。她知道高莲秀不是省油灯,眼光毒着呐,她说自己是小狐狸精,一定是有真凭实据的。她决定帮着高莲秀找找“真凭实据”,脸上找不到,就别处找找看。夜里,进了洗澡间,脱光衣服,让自己披头散发白白嫩嫩地立在镜子前。那时,她确信了高莲秀的说法,自己已经找到了那个“真凭实据”。她比别的女孩发育得早,也发育得更好,这应该跟她的血统有关。她的两条腿又长又直,翘臀,蜂腰,两个乳房小巧饱满,整个人看上去结实而富于弹性。可她又觉得这些还不能算数,至少不够全面。狐狸精媚惑男人主要靠有张狐狸脸,琪琪的脸可不狐狸,下巴不够尖,眼梢不够吊,眼风不够飘。更主要的是眼睛里面的内容。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琪琪的“窗户”透射出来是山青水秀的自然之色,即使有些风吹草动的风情,也是平地一阵风,刮过就算,根本不会狐狸精那样,有计划有步骤地聚敛着打理着挥发着,对男人有做不完的功课。
龙江就是因为这些才跟爹干仗吗?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才被送到省城读书吗?爹的公开说法是,省军区通过和地方政府协调,特别为边防干部开通了一条子女入学的“绿色通道”,可是,据她所知,这条通道早就存在了,主要为战斗在边防一线的干部子女预备的,像她和龙江这样的“二线”干部子女,是排不上号的,再说也用不着,加格达奇已经算是个“大城市”了,这里连师范学院都有,离边防差不上十万八千里,也差着五千四百里,当然,实际的物理距离还没那么远──这些,难道都是跟自己这个“小狐狸精”有关吗?高莲秀说她是小狐狸精,她并不太在乎,相反,心里还有些暗暗得意,倒是因此而断送了龙江的学业,让她心里很不安,也很惶恐。那些天,龙江好像有意在躲着琪琪,她早晨起床时,龙江已经跑出去了。晚上也回来得很晚,一回来就扎到自己屋里,房门紧闭。终归是一家人,哪有不碰面的时候,碰上了,龙江便目中无人般,目光闪都不闪一下,连个偶尔的斜视也没有,当然更不会说话。这哪还是龙江!他可不是个闷葫芦,口水涝着呐,说起俏皮话,常把琪琪逗得哈哈大笑。人也猴精猴精的,常在外面惹出一连串的祸,可末了都是身边那些傻瓜蛋子替他买单。
第二天就要到哈尔滨上学了,行囊也已打理完毕,琪琪希望能跟龙江说上几句话,可他还是一整天不照她的面。直到晚上九点多,他来到她的房间,先是不说话,眼睛往四周乱看一下,然后抓住琪琪的旅行箱提一下说,装的什么破东乱西,这么沉。再拉出拖杆,把箱子在地板上来回拖两下说,这回自己在外面耍单儿了,别动不动就哭咧咧的甩大鼻涕,再哭可没人哄你了。说完,看也不看琪琪一眼,出去了。琪琪心里很不屑,嘁,装得跟个小老爷们儿似的,哪回不都是你惹我哭?琪琪是到了学校才哭的,她哭的主要内容,是悔恨自己发育出一个狐狸精体形,结果把龙江的学业搅黄了。哭过之后,又觉得委屈,心想,又不是我说了算的事,还不是你龙江没事找事!你本来就不喜欢上学,早就跟我说要去当兵?还是你妈向着你,硬说你让小狐狸精给害了,愣往你的臭脚丫子上套拖鞋!这么一想,心里便敞亮了一些。
龙江当了兵,他竟然不是去的黑龙江边防,而是辽南部队的野战军。琪琪比较认真地想这件事,已经是七年之后了,那时,她已经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大三学生,而龙江刚从解放军船艇学院毕业,分配到负责巡航黑龙江水域的巡逻艇大队。龙江绕了一个天大的弯,就为了绕开龙建华一个人,凭一己之力返回了边防。这时候,琪琪才真正明白,龙江那小子果真如高莲秀所说,迷上她这个“小狐狸精”了。不过有一点琪琪始终搞不懂,高莲秀反对龙江和她,可以解释得通──她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她猜不透,可是理解。那么,龙建华为什么要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件事上,龙建华的态度比高莲秀更为坚决,也更为旗帜鲜明,这可有些说不通。虽然说龙建华不是琪琪的亲爹,可他对琪琪的疼爱丝毫不输一个亲生女儿,甚至过犹不及。琪琪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相信,自己是爹的掌上明珠。
一个谜。真是一个谜啊。
第八章
提要:小白在结满霜的玻璃上舔出个透明的圆洞,然后直直地望出来,也就是乌兰这样的大姑娘能干得出来。可是,她哪里知道,七十三个小时之后,她从玻璃上这个霜洞里痴痴凝望的小白,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绝杀战友──叛逃者──的冷血枪手。
乌兰的眼睛从那个“黑又圆”里看出来,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玻璃上的霜不是她用舌头舔化的,是用眼睛看化的,是她目光的温度烤出来的,把霜烤化了。乌兰总是很“热”,脸蛋红通通的,吹透了江风烤了火那种热的颜色,从她脸上总是能看见火光的跳跃。心里也热,心肠热,见谁都是一盆火。当然,她的热主要是针对小白,这谁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她的热是直来直去的,从来不会拐弯。不会拐弯当然就不会月朦胧鸟朦胧,不会飘飘悠悠,是针尖对麦芒,有个结实劲,小白不接招都不行。他们俩那个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小白自己也讲不清楚。他一定是个“受害者”,中了乌兰的热毒了。按规则,当兵的不许在驻地找对象,因此而中枪落马的多了,可小白是个例外,是条漏网之鱼。其实还谈不到什么例不例外漏不漏网的,因为在卡伦这,没有“例”也没有“网”。因为这里有张和平。张和平早就跟我们几个班长交待,让我们跟班里兵透透话,小白是孤儿,不要和他攀比。就这句足够了,咣当把弟兄们嘴都堵上了。
小白在结满霜的玻璃上舔出个透明的圆洞,然后直直地望出来,也就是乌兰这样的大姑娘能干得出来。可是,她哪里知道,七十三个小时之后,她从玻璃上这个霜洞里痴痴凝望的小白,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绝杀战友──叛逃者──的冷血枪手。
当然,我也是枪手之一。
鱼房子这家人没有开门迎客的习惯。当然我们也不是客,下了山,进了院,推门就进。母亲不在,女儿已经从炕上下来了,正在往脚上穿鞋。傻瓜也跟随我们进来了,它很懂事,不像刚才在外面那样又跳又拱,这会儿,乖乖地立在小白身边,瞪着两只大眼睛,有滋有味地看乌兰在那儿忙活。
“山上冷不?”乌兰一边问话,一边歪在炕上,伸手扯过来一个钢盔大的小笸箩,推给我和小白,笸箩里装的是苞米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黑龙江漫长的冬季里,人们普遍拿它当零食。那可不像现在肯德基麦当劳和电影院卖的那种爆米花,是用做饭的大铁锅炒制,炒时先放上沙子,炒子炒热后才放入玉米一块翻炒,炒好后再把沙子筛出去。说是苞米花,其实很难爆出花,清一色哑巴豆子,一咬嘎嘣脆,但满口香。刚才,乌兰一定是一边朝口里扔着苞米花,一边把眼睛贴在玻璃上往外看。
乌兰把苞米花推过来,眼神也跟过来,忽忽悠悠在小白脸上飘。我知道,此时我应该找个借口离开,哪怕只是一会儿。可是,我没有。也没什么理由,就是不想离开放给他们一个独处的机会。那天,小白肯定不想轻易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乌兰,你妈呢?”小白说,“班长想找她讨个方子,狼芽已经两个多月没正式吃顿饭了。”
乌兰瞪大眼睛,不看小白却看着我。“都那么多天了?”
“是。”我说,“从李边疆复员以后。”
狼芽是李边疆带出来的,他这一走,狼芽一下子就颓了,整天焉了巴叽的提不起精神,进食有一搭无一搭,眼瞅着毛皮的颜色败落下去,身腰收缩起来,眼神里的神光熄灭了不算,竟然让眵目糊封锁了大半个眼球。可把张和平愁坏了。狼芽是条好狗,纯种的德国牧羊犬。边防哨所都编制军犬,有定量的伙食标准。狼芽是上级“戴帽”指派给“北方第一哨”的。说来还是指导员姜文清的功劳。他当排长时,是军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军犬繁育基地作过经验报告,他发现基地的17号犬苗甚是了得,血统纯正──根红。表现优异──苗正。德国牧羊犬──祖宗是放羊的,劳动人民出身,整个一个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后代嘛。“北方第一哨”的军犬也要“又红又专”,17号的条件就是一个硬梆梆的合格。于是,他做完报告的同时,也带着17号犬苗的基本情况返回了连队。当上指导员后,姜文清着手做的头件事就是琢磨那个17号,结果他如愿了,“北方第一哨”得到了狼芽,就是先前的17号。狼芽在“北方第一哨”一直优秀着,可自从犬员李边疆复员之后,它的优秀便开始缩水,状态一天不如一天,看这趋势,江河日下的结局已经不可逆转。团里的兽医来看过两次,情况也没有好转。这里的边民世代生活在渔猎环境,有养犬驯犬驭犬的传统,因此也积累了许多土方子,一旦牲畜发病,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招术往往有奇效。我看张和平是病急乱投医了。乌兰家本来养条四眼狗,老毛子那边串过来的品种,有巨灵犬的骨血,大骨架,立耳,凶悍异常,但是,自从乌兰收留了傻瓜之后,四眼就从鱼房子消失了。
“龙班长你吃苞米花!”
乌兰有意把小笸箩朝我身边推。由于用力过猛,小笸箩里面的苞米花剧列地晃动,刷拉拉响,像铁刷子刷锅底,刺得耳朵眼儿麻酥酥的。她这是在推我,推我走。我心里哼了一声,他姐姐的,看在狼芽的面子上,放过你了小白。我伸手去小笸箩里摸了一把,一边把手中的苞米花一个一个朝嘴里丢,一边说:“玛婶在哪儿?”
小白抢着替乌兰答话:“肯定在后面的鱼房子里捣腾挂子。”
我白了小白一眼,不情愿地走出去。挂子是冬季捕鱼专用的网具,下在冰眼里。这种挂网下得不多,通常是一些不甘寂寞的边民才干这个。玛丽娅索和乌兰母女是替公社看守网具的,不可能大冬天到江里下挂子,小白纯粹在那儿顺嘴胡编,目的是开了我。
我往外走时,顺手拍了傻瓜脑袋一掌。“傻瓜,你还傻站在这儿干什么!”
傻瓜愣愣地望着我,不动弹。我不管它,朝屋外走去。我走到屋外,目光一抹,双眼不由得鬼使神差般去看窗户,那儿的玻璃上有乌兰烤出来的“黑又园”。可是,那儿已经不黑了,也看不到圆,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块浅薄的灰白,那是因为“黑又园”已经挂上了一层薄薄的霜花。冬天天短,这儿纬度高,天就更短,才三点多钟,太阳已经让哨所观察架所在的山崖挡住了大半拉。这一挡不要紧,光线被抬高一大块,只能打在乌兰家房子的坡屋顶上,屋檐以下部分沉浸在一片阴冷灰黑的色调里。我的心突地一跳,那个“黑又圆”又出现了,像江里冒出的水妖,妖冶地朝我打着招呼,鬼鬼魅魅地吊我的魂儿。我的脚显然已经擅自作主替我做出了决定,暂时不去后院的鱼房子找玛丽娅索。我径直走到窗户跟前,凑近先前乌兰舔出来的“黑又圆”。我知道,“黑又圆”可以从室内制造完成,也可以在相反的方向制造,站在玻璃的对面,也就是在冰天冻地的外面搞出来。我把我的舌头贴上去,尽量准确无误地吻合先前的“黑又圆”,力争让我的舌头和乌兰的舌头汇合。玻璃冰冰凉,可一下就我让我焐热了,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凉,我想象着乌兰的舌头这会儿也正在对面……乌兰的舌头挺有劲,跟她人差不多,直来直去的,但是很柔软,像泥鳅那样滑来扭去的不肯老实呆着,有股苞米花味儿……很快,我的成果就出现了,我从外面同样用舌头弄出了一个透明的“黑又圆”。下面就应该利用并享受成果了。我把一只眼睛贴上“黑又圆”,看见屋里那两个人正在咬泥鳅。小白的嘴和乌兰的嘴分分合合,好像在从对方嘴里抢东西吃,又像在把食物喂哺给对方,一条泥鳅一会儿在小白嘴里,一会儿又跑到乌兰嘴里。他们抢来抢去,喂来喂去,那条泥鳅竟然没被他们折腾成软面条,反倒更加活跃,反过来折腾他们,弄得那两个人紧着忙活,手脚和全身都跟着用劲,唯恐那泥鳅脱离了掌控,从他们的嘴里不翼而飞。显然,两个嘴已经不够用了,急得火上房可又找不到其它办法,最后,他们只有让他们的嘴互相咬住对方的嘴,再不分开,胶住了一样。
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是个合格的观众。我的合格不仅在于我能够欣赏,并且感同身受地领会和积极参与,尽管我的参与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无人知晓。虽身处室外的寒冷之中,可我的身心和屋里那两个人同样热血沸腾。我能听到我血管里血的流动声音,那是一种江河日下的奔流,带着黑龙江开江时的撞击之声。由于撞击至为猛烈,一些在江底憋了整整一冬天的鱼,竟然被震得蹿飞到岸上。下身那儿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似乎朝前面挺一挺,用点儿劲,就能把乌兰家的房子连同里面的乌兰和小白顶出百丈远。
我的感觉是敏锐的。我感觉到屋里的小白和乌兰正在降温,或者准备转折进行新的一轮升温。我不能让他们在我的眼前干出傻事。我迅速离开窗前,拉开房门,并且把关门声弄得够大,有意慢走几步,再推开里屋的门──帽子落下了。我说。我抓起炕上的棉帽子,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出去。
玛丽娅索开出的方子很简单,给狼芽用两种奶,用人奶点它的眼睛,用牛奶喂它肚子。玛丽娅索这个“二奶”偏方其实并不简单,人奶还好说,到前哨找个哺乳的娘们儿就解决了,可牛奶就不好整了。本来,这一带的边民不少是俄罗斯后裔──玛丽娅索就是个二毛子。他们跟对岸的俄罗斯人一样,有家庭饲养奶牛的传统,但是,这些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奶牛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上的一撮毛一刀切了。公社也基本不饲养,除了发展渔业生产,就是农业学大寨,在沟膛草甸上开荒种粮。倒是对面的集体农庄,家家户户养奶牛,夏天的午后,那些又肥又白的毛子娘们儿晃晃悠悠出来挤奶,从望远镜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她们摇摇欲坠的乳房在那儿忽煽忽煽的,煽出的风压迫着地上的青草,青草显然不堪重负,摇头弯腰,好像还发出唉声叹气的怨声。两国关系松动时,冬天黑龙江封冻,这边常有胆大的人揣上几瓶白酒,从冰面上溜过去,换他们几个奶垞子回来,给家中年岁大的老人当滋补品。其实,这种以物易物的民间贸易从未真正断过,老百姓可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尤其这里的边民,多是内地闯关东的流民,性格粗犷蛮野,加上这地方天高皇帝远,他们才管不了那么多,撒尿掏裤裆,想玩什么鸟就玩什么鸟。双方的贸易建立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方式简单而朴素,买卖双方从来不见面,在约定俗成的地界,各自把物品摆放好,标定好易货标准,然后离开。如果赶巧对上了茬口,你去时你所需要的物件就正好会摆在那儿,就地拿走便是。由于默契,一般不存在占便宜的一头沉问题。对不上茬口,你就把你的东西放好,尽管回家睡大觉,隔一天或几天回来取自己所需要换取的东西。一般一瓶六十度老白干可易三到四个奶垞子,一个奶垞融化后差不多装满一只水桶,十五公斤左右。一瓶白酒还可以换到一条军用皮带,若追加一瓶,就能换到一双皮靴子。现在的边境形势如此吃紧,这种贸易看来要中断一个时期了。如此看来,玛丽娅索的方子我们只能配制到二分之一,剩下那二分之一处于悬置状态,基本没有着落。
回到哨所,我把玛丽娅索的方法跟张和平一说,他说:“我操,知道人奶好使,我提前一年刨坑下种啊,这会儿孩子造出来,我老婆正好在喂奶。”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四班长,你老婆是不是怀上了?算了,你刚结婚,这方面没经验,种没种上你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结婚刚从家休假回来,还没来得及问下高莲秀怀没怀上。我说:“也是,手忙脚乱的,光顾了搂火了,子弹着没着靶我也不知道。”
张和平已经正式向哨所的弟兄们宣布过了,他已经是个“预备父亲”,计划明年一月三号转为“正式”。他老婆是团部驻地十八站林业局的工人,掐指算来,他就是上次回团里开战备会时播下的革命火种。
我说:“人奶好办,牛奶不好办。”
张和平说:“你没问问二毛子,整不着牛奶到底咋办?”张和平从来都叫玛丽娅索二毛子,却不允许我们这么叫,我们只能叫“玛婶”。张和平这是在明知故问。在这儿,是个人都知道,牛奶,老毛子有啊,国境线那边有的是。都知道那边的毛子娘们儿奶子大,她们饲养的奶牛也是大奶盒子,耷拉地,一走,蹭得地皮直冒烟,冬天一个奶盒子挤下来,出的奶能冻成一个标准的奶坨子。可是,要想弄牛奶,就得越境。越境,那可是拿人命往枪口上砸啊。
“玛婶说奶是最好的滋补品,无论人的还是牲畜的。”我说。
“病急乱投医吧,先把人奶搞来再说。”张和平说。
“那得等几天,”我说,“玛婶说了,风再吹几天,地上的雪就瓷实了,她亲自到前哨去给咱们找。”
张和平说:“也是哈,这活儿咱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真鸡巴干不了。”
雪停了,却刮起了大烟泡。不怕大雪飘,就怕大烟泡。大烟泡是很厉害的,呼啸的寒风一猛子一猛子把地上的雪卷起来,一群看不见的饿狼一样,发出阵阵瘆人的嚎叫,在河谷和山林间搜掠。刮大烟泡一定伴随着降温,有寒流自西伯利亚汹涌南下。一般很难分出它们的先后顺序,往往搅成一团胡作非为,放肆得没边,一旦开始作恶,绝不容天地之间再留一丝活气。
大烟泡刮了两天,张和平有点儿挺不住了。不光是我们几个班长,哨所的弟兄们都看出来他心里急。他把自己的酒壶配给了哨兵,又把水壶也灌上了酒,白天就放在窗台上。他不时地走到窗前朝外面张望,望着望着,手就摸上了那个水壶,拧开盖,抿两口。第三天,大烟泡还在刮,张和平的嘴唇上鼓起了黄亮亮的火泡。这是我从未见到的。张和平是啥人呐,天底下还有什么事会让他急成这样?他在我们五连可是位特殊人物,参加过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兵龄比连长指导员还老,要不是因为打兵受过处分,加上嗜酒如命的毛病,早就提上去了。可是也怪了,这个“问题排长”偏偏就“卡”在卡伦,上上下下都没有要挪开他的意思。唯独指导员姜文清提出过把他换下来。他一直认为张和平是个容易“豁边”的人物,别人敢想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他也敢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捅了大娄子,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别人。可是,姜文清的意见却让团里给否了。姜文清对我不错,一次向我透露,连里有意让我接替张和平代理哨长职务,这样就可以把我直接报到团里作为“干部苗子”,为提干创造条件。我大体知道团里为什么不同意换下张和平的原因。卡伦这地方太特殊太重要了,出了事基本就通天,一般人是镇不住的。玛丽娅索的爷爷当年就是岛上卡伦的卡兵,当时的卡长都是由被朝庭招安的惯匪头目担任。试想一下,背后是粗横蛮野的关内流民,面前是杀人不眨眼的异国强盗,得有敢称王称霸的气魄才能在此立足。用现在的话讲,要有很强的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张和平这个人,身上什么都有可能稀缺,就这个能力不缺。哨所有他在,兵们夜里睡觉都会踏实很多,用现在的话讲,绝对是个气场超强的人物。
可是,现在他的能力有点儿不管用了。
大烟泡刮到第四天,晚上停了,可是天还阴着,天气预报说还有雪。张和平对我说:“哨所的情况得向连里报告一下。菜已经断了几天了,不能天天让弟兄们拿筷子蘸酱油下饭,想办法回连里一趟,哪怕是弄些蔬菜罐头回来也好。”
这事还得我和小白去干。
临行前,张和平把自己的皮手套丢在小白怀里。他的手套戴上没几天,好像是一周前才戴上的,而小白的,布面早磨坏了,里边羊皮的皮板也磨破了,露出了白花花的羊毛。小白摘下自己的破手套扔在床上,戴上张和平的新手套,双手合拢,拍打着,“换了噢!”。
那天,张和平是送我和小白出门的。小白抢先一步从陡坡那里出溜下去了。我正要随着下去,张和平突然拉了我一把,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可是欲言又止。奇怪了,这可不像是张和平。他咳了一下,是干咳,显然肚子里有什么话被压制下去。他跳开目光,看着远方乌蒙蒙的天际,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张和平随意地说,“假如卡伦就咱俩人,哨所又断粮了,你又病得快要死了,我该咋整?”他的随意状做得水平不高,不做还好,一做,反而更像做了,是做作,破绽明晃晃搁在那。我听出了一种掩饰,一种刻意,是随意掩盖下的吃力和大费周章。可是,当时我并没在意,或者说没有留意他的刻意。我随口应道:“怎么可能,一哨之所,怎么能就咱俩?”张和平哈哈一笑:“也是哈,就咱俩那叫岗哨不能叫哨所。”
我和小白从陡坡上下去后,从乌兰家借个爬犁拖上,沿着江堤往前哨走去。江堤上的雪尽管也厚,但有强硬的江风日夜不停的吹打,还是比别的地方瓷实,勉强能托住人,可以走。连里也在为给养上不了哨所的事犯愁,如果雪再不停,准备人背肩扛从便道运上去,再从鱼房子那儿拿绳子吊上哨所。我找了几个家里富裕的兵,询问谁手里有奶粉。又找两个上海兵,问他们手里有没有大白兔奶糖。没有奶粉有这个也凑和,听说三块大白兔奶糖就能泡出一杯牛奶。有了牛奶,哪怕是代用品,说不定也能救狼芽的命。可是,我扫了一圈,空手而归。
吃完中午饭,我们不敢耽搁,带上连里军医老高给的药,把几箱马口铁罐头放上爬犁,赶紧往回赶。姜文清把我们送出营门外。“让你们排长消消火,连里会派人接电话线,给养连里也会想办法送上去。”姜文清说话时,不时地望着乌沉沉的天空,脸上堆累的乌云并不比天空上薄多少。我知道,他的担心不只是天气。他一直想把张和平换下来。对我们那个爱喝酒的哨长,他有一种本能的戒心。张和平也非常不待见姜文清,公开对我说过,那个人假,太能装逼,你跟在他屁股后拣不着一泡好粪。我心想,你这个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家伙,怪不得提不起来。
我和小白拖着爬犁走到前哨,再拐上江堤,雪就下起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前面的卡伦岛成了一团模糊的暗影。我停下来,检查了一下冲锋枪的枪机,天气太坏了,我怕大栓会冻住。小白也检查了他的枪。他还把弹夹卸下来,故意亮给我看一眼。他这是在嘲弄我的小心。我心里哼了一声,你懂个屁,我们可能早就被对面那帮哥们儿套进了AK47的准星。即使不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也落进了他们的观察镜里,并在他们的观察日志上被记录在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军队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先后两次出现在卡伦岛附近的江岸,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也是张和平迟迟不往连队派兵的原因。两边的弦儿都绷得太紧了,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弄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静。
雪,小了。
我们抵近了卡伦岛下腹部的江堤,这儿距离岛子最近,明水期三十二米,现在是五十米左右。忽然,眼睛里撞进一个什么东西,模模糊糊的一抹绿色,一闪,不见了。我调整了一下视线,眼前一片白茫茫,什么也没有。可是,我的眼睛不会欺骗我,它也不会被这白茫茫欺骗,一定是什么活动物体触动了我的目光。我的视线码着卡伦岛的边缘一寸一寸地搜索。这时,雪基本停了,视野通透了一些。我的视线最后卡在了一撮毛。一撮毛大约有二十平方米,是卡伦岛边缘的一个小土墩子。此时那个人已经移动到了一撮毛,再往前,就进入卡伦岛的腹地了。
“有人越境!”小白也发现了目标。
我和小白立即原地卧倒,朝岛上观察着。小白捅了我一下,示意我朝雪地上看。原来我们趴卧的雪地上有几个不规整的凹痕。细一看,那凹痕其实是很规整的,只不过是这场雪作乱,弄模糊了。那是人的脚印,是直奔了江堤下面去的,就是说,是已经上了岛的那个人留下的。
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
该不会是个叛国投敌分子吧?
我和小白没有丝毫的迟疑,从背后顺下冲锋枪,一个滚翻下了江堤,然后观察一下,以匍匐姿式朝各自的隐蔽物爬过去,隐蔽好。我们已经大致看清了那个人的身影。难怪刚才看不清楚,那个人身上的皮大衣是反穿着的,一身白花花的羊毛起到了极好的伪装效果。可是,他的裤腿露出了一截,就是最初撞到我眼睛里的那一抹绿色──他是个军人?!因为他反穿着皮大衣,又卧在雪地上,我们根本无法弄清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也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即使他不是军人,也一定跟军人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不敢多想下去。我们的视线死死咬住那个人。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个军人,那俯卧的身形和姿式,分明就是个训练有素的兵。
这时,小白低声啊了一声。听到他这一声“啊”,我的头皮也一阵发麻。
作者简介
王伏焱,艺名:十二郎,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青冈县人。
当过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指导员,在团师旅军政治机关当过干事,先后在沈阳军区电视艺术中心和武警部队文工团任编剧。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高雪部队》、《高地纪略》,长篇小说《从这里到永远》、《越境》,电视连续剧《士官》、《陆军·陆军》,话剧《大江流》及油画等美术作品。
小说集《高雪部队》入选“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小说《像飞一样》被编入0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
作品多次获奖。
投稿请寄:
dajunmao
.北京中科白颠疯曝光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的医院最好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cs/87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