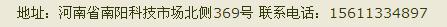长篇禾村之五汪亚梅
汪亚梅长得如何漂亮,我就不说了,连全镇的文盲都跑到我们教室窗户来“听课”了。
高一时,我转学了,转到邻近的一个县去读书。有一天,学校里多了一位女老师。
她的名字马上就传遍了小镇。
关于汪亚梅的漂亮,我就不多描写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吾校本来就是一潭死水,突然被烧开了一样,到处都冒着沸腾的旋涡。
我们张老师,因为在省报上发表过几首新诗,一向以当代徐志摩自喻,很看不起别人,又不太修边幅,最近不仅穿戴工整,而且主动在校园内组织一个文学社,出版起校园诗集来,还在他一向看不起的油印刊物上,一连发了六七八个诗组。专门送给汪老师,请她指点。
平时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不太读张老师的诗,现在,公然在公共场合激烈地抨击张老师的诗组。未婚且长得帅气的刘老师,甚至对事不对人地宣称——所谓新诗,不过是手淫,因为新诗如何产生高潮,何时达到高潮,只有诗人自己才清楚。
大约过了十天,兰木镇赶集,也变得空前的热闹起来,集市本来是交易物品的地方。但这个集市变了味,许多人甚至不是来赶集的,借着这个机会挤到我们学校来,目的就是看一眼汪亚梅。连文盲也跑到我们学校的窗户边来“旁听”了。
传达室的老方顿时成了人物,经常可以听到他在呵斥别人——站住站住!教学重地,闲人免入。
我们学校的于芳老师也漂亮,但笑起来就肆无旦忌,隔着一条街都听得见,有时甚至和男老师一样说粗口。镇上邮局那个女的,眼睛总是凶巴巴的,好像一个女人只要拥有了一张好脸蛋,就可以把别人的欣赏当成好色,把我们这些经常去邮局的孩子的尊严踏在脚下,比如我问:喂,有《故事会》吗?她眼睛看都不看你,冷冷地说:自己找。
汪老师不然,她的眼睛细细的,总含着笑,像这个世界的春天全装在她的眼里,又好像这个世界因为有她,也总是阳光明媚。汪老师甚至分不清别人是看她,还是垂涎的她的美色。比如她走在大街上,几个社会上的泼皮无赖躲在她的后背某一处,集体意淫般调戏地叫她:汪亚梅——汪亚梅——,如果是我们的于芳老师,一听就会回头泼辣地骂道:叫死啊,叫你娘啊。
汪亚梅不然,她会突然地立住,回头去寻找声音的方向,眼睛里仍然含着笑,直到发现那一群恶作剧的泼皮发出“哈哈哈”的狂笑之后,她才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飞快地逃走。
她住在教学校的二楼一个小阁楼上,那个小阁楼别的老师也住过,住过也住过,不见得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汪老师住上去之后,就在阁楼的窗户上伸出一个铁架,铁架上养了两盆指甲花。秋天里,那两盆花一开,像两团红色的火焰。
汪老师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也罢了,偏偏还能操一口流行的英语,有一次,听说县里来了几个外商,就把我们汪老师借去用了两天。这个事让我们心神不定,汪老师不在学校的那两天,我们好像这个世界的末日来临了。同学们私下相互打听,汪老师会不会调到县里去工作。
两天后,汪老师回来了。
县上也有调汪老师去工作的意向,可汪老师不同意,她愿意蹲在这山沟沟里。上面也没办法,因为她是来支教的,一定三年。她自己要求到山沟沟之类贫困的地方去,三年过后,她会走。
当然,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天真地以为汪老师会永远留在镇上。
汪老师永远留在镇上,也不是没机会。除了校长老师对她非常的欢迎外,连一向挑剔别的美女的于芳老师也喜欢上了汪老师。她觉得汪老师特别会打扮,就常常上小阁楼去与她交流服装如何搭配的学问。我们这些学生也非常喜欢汪老师,如果是别的什么漂亮女老师,学生中调皮的人总喜欢在背后说她的坏话,但汪老师,总让别人说不出口。她的清纯与美丽,像一只清洁剂涂在你的嘴唇上。
另外,最最让我们喜欢的是,她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英语本来难学,她说不难。上课让我们做游戏。让我扮汤姆,另一个同学扮杰克。汤姆问:你到哪儿去?杰克答:我到学校去。大家反复学这一句。学会了,她又让汤姆问:你昨天到了哪儿去,杰克说:我昨天去了学校。她又让大家反复读,学会了。她再让汤姆问:你明天准备到哪儿去。杰克说:我明天准备到学校去。她又反复让我们读,直到读会这一句。然后,她就教会了我们过去式,现在进行时,将来时的语法不同点在哪儿。
她教课文也与别人不同。早自习到了课室,就带领大家高声读。你读不准也没关系,一定要高声。她说:英语是一种语言,不是数学,不是1+1=2。语言的特点是约定俗成,你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它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这里是用“Of”,那里用”For”。
我们喜欢跟汪老师高声朗诵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声音像天簌。清脆得一声出来,把你的五脏六腑洗了个干干净净。所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和汪老师成了朋友。下了课还围着她问这问那。几个大胆顽皮的男生,有时就闯到她的小阁楼讨水喝。她一点也不嫌麻烦。后来,有男生告诉我,说汪老师专门准备了凉开水供大家喝。我们班的同学自然把她的阁楼当成了学校的开水供应站。甚至可以说——我们男生有时候明明不要喝水,特别是冬天,喝多了难得上厕所,可宁愿多跑几趟,也厚着脸皮说口渴。
有一天,杰克突然喝着喝着,大叫一声,说:有点香。我喝了一口,说:真香。他又喝了一口,说:还甜。我再喝一口,说:是甜。
细心的汪老师把白开水换成了甘草水。
杰克后来不知从哪里打听了一条消息,公布了汪老师是来支教的。这让我们同学们集体都郁闷死了。原来汪老师是要走的。后来,我们公推胆大的杰克当面问汪老师。
这一节课当然是英语课。上到三分之一时,她提问了。大家回答得很正确。她就笑了,说:我看你们大多数人从不喜欢到喜欢,进步很大嘛,英语是不是并不难?这时,我捅了一下杰克。杰克就举起手。汪老师发现了他,问:谭伟,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嘛?
谭伟说:我叫杰克。
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
汪老师也笑了,抿着嘴,偏着脑袋,望着他。显然,她太高兴了,一个老师能把自己的课教得这么深入人心,谁都会得意的。
谭伟说:汤姆要我请问你,你是不是教了三年就要离开我们这儿?
这个问题在同学们中已私下议论过许久了,是大家一直关心的。只是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汪老师不急,她走近我,但是偏着头,火辣辣的眼神望着我,问:那就叫你汤姆吧,汤姆,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敢主动提?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汪老师说:以后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了,每一个同学想提问,只能自己提,请别人提就是胆子不大。汤姆,你说呢?
我嗓子眼发出了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
汪老师笑吟吟地说:汤姆,望着我的眼睛。
我是多么想望着她的眼睛,望上一整天我都愿意,但现在我怕。我仍然低着头。汪老师说:汤姆,抬起头,大家一起来,都望着我的眼睛。
所有的眼睛望着她,她说:跟我念:ILOVEYOU。
课堂上响起整齐划一的声音:ILOVEYOU。
她说:同学们,你们喜欢我,我也爱你们。我确实是自愿来支教的。但,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种生活,并不说这里的环境,而是你们。跟我念:ILOVEYOU。
美丽的汪老师并不是说着玩的。她有时候也开玩笑地学说我们的方言了,大概是为了听懂商贩的话,好和他们讨价还价。学校后面有块菜地,是附近村民送给老师的,很多老师都种了蔬菜。汪老师也要了一块,课余搞起大生产运动来。还有当代徐志摩在《诗刊》上发了几个诗组。听说汪老师和他有点意思了。
总之,汪老师喜欢上了我们这个小镇,她在努力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像要把根扎在这里一样。
冬天里下了一场雪。满世界成了一个颜色。白得让人心颤。周五的时候,汪老师提议去滑雪。放学时,她问,谁愿意去?结果班上好多同学都愿意。第二天是周日,我们不上课,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和我们读寄宿的一班人去香炉山滑雪。
张老师刘老师于芳老师都是本地人,所以滑雪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汪老师是上海人,就只能由我们这班同学教她了。教了她大约一个钟头。她就开始自己学着从山坡上往下滑。那班男老师想来当护花使者。汪老师却大声叫道:我有学生——你们滑你们的吧——她始终把我们当成她最好的看护人。
开始——不知谁叫了一声,几十张雪铧就象离弦的箭射向山脚。四五个男同学伴随在汪老师的周围,从远处看,就像一只张大翅膀的大鸟向山脚展翅飞去。雪花被犁开,象些精灵古怪的天使飞舞在我们的周围。
冲啊——
好美啊——
我飞起来了——
许多的叫喊声与雪花纠缠在一起,在山腰上亲吻。
杰克来了——谭伟自己大叫一声,一个人施展起他的技能,像空中飞人一样,丢下我们,向山脚的盆地冲去。我担心汪老师,一直不离左右。果然,她好像控制不住地向我这边冲来,我知道她会撞上我的,便施展起功夫,向左一避,伸出手一把拽住了她,但惯性大,我被她带着向侧面冲去,然后,我们就双双摔倒在雪地里。还是不行,她的身子往前一滚,连带我也往前面滚去。
山坡上两只手联成了一条直线。上面一个雪球是我,下面一个雪球是她。一个雪球盖过了另一个雪球。另一个雪球又盖过了原来那个雪球。两个雪球慢慢就融成了一个雪球,从山坡上朝下滚去。下面的人看呆了,一会儿大声鼓起掌来。
这次滑雪很愉快。但也有个不好的结果。我们那个很帅很帅的刘老师,也许是为了展现自己身体好,穿得很薄,在雪场上确实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肌肉男的健美,但回去以后就冻伤了。先是感冒,后来感冒牵出大毛病,犯了肺炎,医院,听说要住上半个月才会好。
这也没什么,治治就会好的。但他教我们的生理卫生。所以学校决定另一个老师来代刘老师的几场课。在周前会上,汪老师主动说她来代。几位年纪大的老师立即赞成。一则生理卫生并非主课,谁代都可以,二则滑雪也是你汪老师提议的,当时一起高兴了,就有责任收拾残局。
汪老师除了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外,又成了我们的生理卫生老师。我们倒是高兴,巴不得她语数英物理化学全包了。所以,汪老师上这门课,我们不仅不觉得特别,希望刘老师以后不要来上这门课就好了。
果然,刘老师这人看起来强壮,似乎徒有其表。肺炎快好了,牵出十二指肠溃疡,要动手术,手术之后要恢复,学校就不得不作了调整,汪老师就正式成为我们生理卫生老师了。
一切都好象没有别的意外。日子也过得飞快。
很快,我们班上就有点特别,大家心照不宣的特别。因为生理卫生上完第九章了。第十章叫《生殖系统》。那时,我们这些青春期萌动的男女,对这一章既感到特别新奇,也特别敏感。我可以说大家在新书发下来之后,就个个偷偷地看过无数遍了,但真的要面对这一节课,大家都没有勇气。
不仅是我们没有勇气,连学校也没有勇气。在我们那个山沟小镇,听说所有的生理卫生老师都羞于将“子宫、阴道、阴茎”这些下流词说出嘴。所以,按照老办法,这一章通通用“同学们自习”来对付。到了下一周,老师就直接讲第十一章。
别的班进度比我们快,第十章果然是采用老办法。跳过去了。我们这班也希望跳过去。因为万一要讲,按汪老师的教学方法,叫谁站起来回答她的问题。比如:女性生殖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打死谁,谁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回答。
我们也相信,这么漂亮,这么年轻,这么一个没结婚的女老师,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嘴里不断地冒出“阴茎阴道输卵管”之类的单词。尤其是我,特别坚信,这些下流词从她嘴里打死也吐不出。
谭伟问我:那节课会不会上?
我说:别的班不是自习吗?
刘伟说:我和学习委员换个位子,他同意了。
我知道学习委员没有发现谭伟的阴谋,换到后面,老师一般不会提问。又想,连谭伟也害怕上这节课,其他人就不必说了。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汪老师走进教室,在“同学们好”“老师好”的礼节之后。汪老师脸色微红,眼睛含笑,望了一遍大家,说:今天怎么啦?都叭在课桌上,我说一二三,大家把腰挺直。
同学们都笑了。一二三之后,大家在她严密的注视下,都挺直了身子。她再望了一眼,说:大家说,谁是班上最大方的同学?
我的天,这节课她真的要上了。为了逃避提问的命运,有人大胆地冒了一句:谭伟。
全体兴奋起来。说:谭伟,谭伟。
汪老师用眼睛搜索了一遍,问:谭伟呢?
谭伟早已缩到课桌下去了,但还是被她发现了。她说:谭伟,你站起来。
谭伟见躲不过,只好站起来。汪老师说:你大声地说一遍,我叫杰克。
谭伟低头低声地说了。
汪老师说:不行,大声点,上次你不是说得很自信吗?
谭伟豁出去了,大声叫道:我叫杰克。
汪老师说:这就对了。今天,我就不会提你的问了,会提谁的问呢?现在不宣布。
全体紧张起来,只有谭伟活了,朝这个做个鬼脸,朝那个挤挤眼睛。
汪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方钉上一个钉子,然后将一幅卷轴挂上。她的手托着卷轴慢慢地往下放,一幅图就徐徐打开。
决不是一幅写意山水。
左右两边分列着男女生殖器示意图。
所有的头都缩进双手抱成的圆圈里。
谁把头低着,我就向谁提问。
所有的头一律抬起。
汪老师说:同学们,你们感到羞耻吗?你们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你们都是父母生养的。你们最初是住在这个地方。它叫子宫。这是你人生最开始的第一个家。对于我们的家,我们会讨厌它吗?
胆大的同学说不会。
汪老师说:这就对了。那么,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由一个卵子与一个精子结合而产生的。精子在什么地方产生呢?在这里,她用教鞭指着阴囊,继续介绍道:在这里产生。卵子呢,她用教鞭指着卵巢,说,另一半就在这里产生。
她没有要我们站起来回答,她一边讲解,一边自问自答。她好像跟我们讲水分子是两个H,一个O组成的一样。很快,我们就镇定下来。这一切,当然缘于她的坦荡。她的课,就像涓涓细流,流过我们荒芜的心田,又像潺潺溪水浇灌着我们干裂的心事。还好像她有魔法一样,那些平时羞于启齿的名词,用她清脆的声音念出,变成了我们身体的可爱的一部分。最后,她讲完了,就说:我说不提问,是骗你们的。下面我要提问。谁呢?
大家虽说可以听汪老师讲解,但要自己也来说这些名词,还是羞于说出来。一个个又紧张起来。
汪老师说:大家准备一下,问题是“什么叫十月怀胎”。
这个倒不难,但同学们还是怕叫到名字。
一会儿,汪老师才说:刚才是谁提谭伟的名?
大家全松了一口气,说:郝一全。
汪老师玩笑说:你想出卖谭伟,你就要承担代价,同学们说对不对?
大家起哄:对对对——
汪老师说:给郝一全一点掌声好不好。
掌声格外热烈。
我相信你,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汪老师眼睛含笑,很真诚。
我只好站起来,豁出去了,说: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在母亲的子宫里,需要经过十个月的发育才能诞生,这个过程叫十月怀胎。
请再一次给一全同学掌声。
掌声又响起来了。
汪老师说:一全同学带了头,我们每一个都要说一遍。题目叫我从哪里来。同学们勇敢点。
有人开了头,其他人就不至于太那个了,甚至有的人说得比我还完整。气氛就渐渐自然了。也渐渐活跃起来。谭伟的调皮劲在这个环境中调动起来了,甚至问:那么双胞胎呢?
汪老师又讲了双胞胎的来由。
课真是上得太好了!
原来生理课也是可以这样上的。
别的班的同学很羡慕我们,但羡慕归羡慕,我们觉得汪老师不应该给他们去补这一课,谁叫你们运气不好呢。不久,刘老师的病就好了。他又可以来上课了。可我们总是怀念汪老师上生理卫生课。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刘老师病生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汪老师用这种全新的形式,与坦荡的精神上《生殖系统》这一章,让校长大发感叹,在周前会上表扬了汪老师。其他老师也好奇,虽说听同学们讲,汪老师这节课确实上得好,但百闻不如一见。校长说:那就让汪老师给所有老师上一场公开课。我们一定要破除以前的陋习,学生都十六七岁了,捂着盖子怎么行?就要让他们正确认识青春期问题。
当然,我们做学生并不知道老师们开会的精神。只是有一天,第四节课是生理卫生课,却突然通知我们班的同学到大会议室上课。大会议室可以坐两百人。我们进去,后面早已坐满了几十个老师。弄得我们吓了一跳。走上台的是汪老师。
汪老师眼睛含笑,说:同学们,今天是全校老师来听我们班的公开课,这场课我们已经上过,是《生殖系统》一章。希望大家和平时一样,踊跃回答问题。好不好?
好——我们一齐回答。
我们都有一种集体荣誉感。再说,公开课的意思我们明白,就是对上这场课的老师教学水平的一种肯定。也就是示范。不说是汪老师,就是其他老师,我们也应该给他争气。
在场的老师都吓了一跳,上这样高难度的课,下面也气壮如牛,回答得如此整齐,可见汪老师教学很有一套。
汪老师也像平时一样,很快进入了角色。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我被叫起来了。如果说第一次有些被动,则这一次我真想让汪老师叫我。因为,我觉得一点也不难。因为汪老师叫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回答过,事后也没有人讥笑我。所以,我一点也不慌,完整地回答了她的提问。
刚刚答完,后面老师们自发鼓起掌来。
汪老师更加自豪,下半场讲得更加行云流水。同学们也入了境界,回答问题十分踊跃。
这场公开课就史无前例地取得了成功。
过了半个月,我们又接到了班主任的通知,全体同学到大会议室集合。
这次阵容更大,学区主任知道这件事了,要听公开课。带来的教师队伍更为宠大,全学区的生物老师,加上学区的领导,黑压压地坐满了后面几排。
仍然是汪老师上《生理卫生》课。
气氛仍然是那样热烈。
汪老师可是出名了。我们为她高兴,为她自豪。
很快,就进入了期末复习。这一天,我们又突然通知到大会议室集合。这次是县教育局的领导来了。校长非常隆重其事地作了开场白,他说:司马局长非常关心我们学校,亲自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听我们汪老师讲课,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局长给我们作指示。
局长说:具体的教学工作有分管局长管,我也多年没有听公开课了。这次学区李主任向我汇报,我觉得十分高兴,局里的领导听了,大家都高兴,不管分不分管这一块的同志,大家都愿意来听汪老师讲课。可以说局党委的同志都来了。这是件好事……
汪老师这场课也讲得很认真,掌声不断。
过了三天,我们又被通知到了大会议室。市局局长来听课了。
汪老师开始讲课。她还是那样讲得深入浅出,但我们同学们没那么兴奋了。过不了几天就要上公开课,要站起来回答问题,嘴里尽是些“精子卵子”之类的词,说多了也无味。难免不像开始时那么有劲了。
过了几天,有些老师也有些议论,说上面的领导平时不见得喜欢听公开课,怎么现在这样喜欢听了。甚至谭伟的父亲也找上门来,说谭伟的成绩本来就不好,怎么老是安排公开课,何况总是讲并不重要的《生殖系统》一章,其他主课还要不要学?
这天,校长到了我们班。教我们班的教师也全数到场。他说:同学们,不要有厌烦情绪,汪教师讲课有名气,是为我们学校扬名嘛,有什么不好?大家都来
转载请注明:http://www.nolkr.com/wahl/12724.html